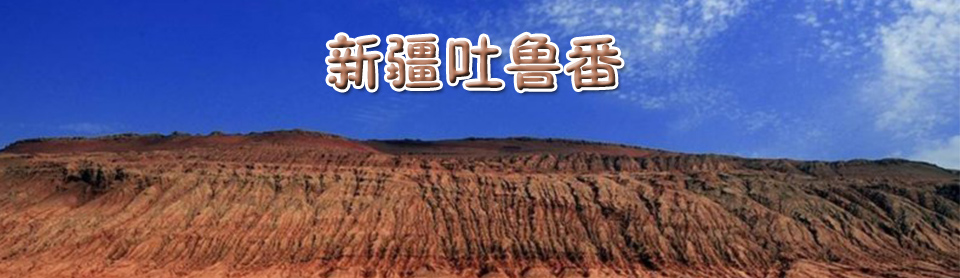唐代诉讼文书格式初探以吐鲁番文书为中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诉讼文书采用什么格式,在史籍上很少记载,即使不多的一点记载,也因语焉不详,多有矛盾,而一直为我们所不明。正因如此,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也不多,似乎还没有专门的论着出现。
最近,有陈玺《唐代诉讼制度研究》问世(以下简称为《诉讼制度》),书中在第一章第二节《起诉的程序要件》中,列有《唐代律令关于起诉程序之一般规定》与《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二小节。在前一小节中,作者指出:“唐代诉讼实行‘书状主义’原则,当事人诉请启动诉讼程序,均需向官司递交书面诉状”。这里称唐代诉讼文书为“诉状”。又引复原唐《狱官令》35条及唐律,认为“唐律严惩代书辞牒诬告他人之行为……若于他人雇请代书诉状文牒之际,加状不如所告,但未增重其罪者,依律科笞五十”。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诉状文牒”。作者还说:“刑事、民事案件诉事者在向官府告诉前,均需制作诉牒,作为推动诉讼程序的基本法律文书。法律对于诉牒的格式与内容均有较为严格的要求”。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诉牒”。作者举了几个例子,说“其中皆有辞状文书作为有司论断之基本依据”。这里称诉讼文书为“辞状文书”。
这样,我们在该书不到3页的篇幅上,就看到作者对诉讼文书有以下几种不同称呼:诉状、辞牒、诉状文牒、诉牒、辞状文书。甚至在同一句话中,可以前面称“诉牒”后面称“诉状”。此外还有“辞状文牒”、“诉牒辞状”等说法。其中如“诉牒辞状”并列,作者写为“诉事人递交的诉牒辞状”,则不知二者是一种文书,还是两种不同的文书。
这种混乱,实际也说明了诉讼文书在唐代称呼的不确定性,以及使用时的混淆。那么,到底唐代诉讼文书在当时如何称呼?它在实际使用时有无变化?其格式究竟如何?就成了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二、唐代法典中的称呼
首先我们要看看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有怎样的称呼。《诉讼制度》引用了唐代法典中的一些条文[,但论述的重点不在诉讼文书的称呼上,即没有明确指出法典对诉讼文书的具体称呼。现在让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唐代法典的相关条文。
1、复原唐《狱官令》35条前半:
诸告言人罪,非谋叛以上者,皆令三审。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虚得反坐之状。每审皆别日受辞。(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别日受辞者,听当日三审。)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司。
按:此条唐令是根据《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通典》卷一六五《刑法》三《刑制》下,以及《天圣令》宋29条等复原而成。令文中称诉讼文书为“辞牒”;称接受诉讼文书为“受辞”或“受辞牒”。
2、唐《斗讼律》“告人罪须明注年月”条(总第条):
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官司受而为理者,减所告罪一等。即被杀、被盗及水火损败者,亦不得称疑,虽虚,皆不反坐。其军府之官,不得輙受告事辞牒。
疏议曰:告人罪,皆注前人犯罪年月,指陈所犯实状,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但违一事,即笞五十,谓牒未入司,即得此罪。官司若受疑辞为推,并准所告之状,减罪一等,即以受辞者为首,若告死罪,流三千里;告流,处徒三年之类。……“其军府之官”,亦谓诸卫及折冲府等,不得輙受告事辞牒。
按:此条律文称诉讼文书为“辞牒”或“告事辞牒”。接受诉讼文书者为“受辞者”。诉讼文书不实,为“疑辞”。又称呈递“入司”的文书为“牒”。另外要注意:律文中所谓“准所告之状”中的“状”,指“实状”即情况、事状,而非文书形式之“书状”之义。
3、唐《斗讼律》“为人作辞牒加状”条(总条):
诸为人作辞牒,加増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疏议曰:为人雇倩作辞牒,加增告状者,笞五十。若加増其状,得罪重于笞五十者,“减诬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为人作辞牒增状至徒一年半,便是剰诬半年,减诬告一等,合杖九十之类。
按:此条律文亦称诉讼文书为“辞牒”,可以雇人书写。如果在辞牒中增加所告罪状,要笞五十。律文中的“状”是“情状”“罪状”之意,也不是文书形式之“状”。
以上是法典中关于诉讼文书最基本的条文,从中可知,在唐代法典中,对诉讼文书最正规最严谨的称呼,应该是“辞牒”。从其中“受辞”、“受疑辞”看,又以“辞”为诉讼文书的大宗,其次为“牒”。
法典中也有“状”,例如“辞状”、“告状”等,但正如前面所说,这里的“状”都是情状、罪状,即文书内容,还不是一种文书形式的意思。
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辞》
《诉讼制度》重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的诉讼资料,在《出土文书所见唐代诉牒之格式规范》一小节中收录了诉讼文书(书中称“诉牒”)23件,为我们研究诉讼文书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作者没有区分“辞”和“牒”,使用了一些“状”,未能讲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复原出“辞”和“牒”的格式。凡此种种,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关于“辞”和“牒”的区别,是研究唐代文书制度者的常识。但相关资料其实有些差异。常引的是《旧唐书·职官志》所云:“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上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也。)”。这其中的“有品已上”,《唐六典》作“九品已上”,是史料的差异之一。此外,引文的注中说“非公文所施,有品已上公文,皆曰牒”,文气不顺:既有“皆”字,当言“公文及非公文所施,皆曰牒”才对,否则“皆”字没有着落。《唐会要》没有“非公文所施”字样,作“下之达上有六(上天子曰表,其近臣亦为状。上皇太子曰笺、启。于其长上公文,皆曰牒。庶人之言曰辞”。到底哪种说法正确,现已无法判明,就“辞”“牒”的区别而言,起码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有品的官吏所上公文曰牒。二、庶人之言曰辞。至于是“有品”还是“九品”,从实际使用的例子看,似应以“有品”为是。如果上文推测的“皆”字与公文和非公文的联系有道理,则有品官吏所上公文及非公文皆曰牒。简单说,在上行文书的使用上,品官(含职官、散官、勋官、卫官等)用“牒”、庶人用“辞”。这一区别也适用于诉讼文书场合。
关于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中村裕一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过研究。他在《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五章《吐鲁番出土の公式令规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四小节《辞》中指出:辞式文书是庶民向官府申请时用的文书,实例只存在于吐鲁番文书中,应该为《公式令》所规定。《辞》在北朝已经存在,传到高昌成了高昌国的《辞》,也为唐代所继承。唐代《辞》与高昌国《辞》的区别是后者没有写明受辞的机构。《辞》的文书样式是:开头写“年月日姓名辞”,结尾写“谨辞”。书中列举了六件唐代《辞》的录文。
中村裕一的研究已经涉及唐代《辞》的主要方面。本文要补充的,其一,是将《辞》的格式更完备地表示出来。其二,补充一些《辞》的文书,并作简单分析。最后,总结一下《辞》的特点,以便与作为诉讼文书的《牒》进行比较。
完整的诉讼文书的《辞》,应该具备以下格式:
年月日(籍贯身份)姓名辞
标的(即所诉人或物)
受诉机构(一般为:县司、州司、府司、营司等):所诉内容。结尾——谨以辞(或咨、状)陈,请裁(或请……勘当;请……)。谨辞。
(实用诉讼文书,后面附有判词)
吐鲁番文书中的《辞》,仅就《吐鲁番出土文书》一至十册统计,有近30件,若包括案卷中所引的《辞》,约有40件之多。以下举几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例子。
例一、唐贞观廿二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
此件《辞》严格说不是诉讼文书,而是申请书。是米巡职向庭州提出的申请,目的是希望发给他公验,好去西州贸易。处理此件《辞》即写判词的“怀信”,应该是庭州的户曹参军事[24]。此件《辞》的申请人,应该是一般的庭州百姓。
例二、唐永徽三年()士海辞为所给田被里正杜琴护独自耕种事
此件《辞》是某士海上诉至县里,说本应给自己的田地被里正耕种,请县里核查处理。“某士海”应该是一般百姓。
例三、唐麟德二年()牛定相辞为请勘不还地子事[26]
此件《辞》是牛定相上诉县里,要求调查樊粪?塠五年不还他地子的原因。县里接到《辞》并审理后,县令或县丞某“果”下判词,命令坊正带樊粪?塠到县里接受询问并与牛定相对质。以此件《辞》来上诉的牛定相,应是一般百姓。
例四、唐总章元年()西州高昌县左憧憙辞为租佃葡萄园事
此件《辞》是左憧憙上诉县司,就一所葡萄园的租佃纠纷,请县里出示公证(公验)。上诉者应是一般百姓。
例五、唐仪凤二年()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辞为诉男及男妻不养赡事
例六,唐永隆二年()卫士索天住辞为兄被高昌县点充差行事
此件《辞》是军府(前庭府?)卫士索天住上诉至西州都督府的诉《辞》,说自己的兄弟索智德已被点充府兵,请都督府牒下高昌县告知。上诉人是府兵的卫士。写“付司”的“伏生”是西州都督。前引唐《狱官令》云:“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司。”此件文书的处理则是先“付司”,通判官给出意见后,长官批示“依判”。给出具体意见的通判官“待举”是西州长史。当然,所判意见针对的其他几件诉《辞》,因文书残缺而不为我们所知了。
例七,唐景龙三年()严令子妻阿白辞
此件《辞》是《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的一部分。案卷有“高昌县之印”数方,因此本件《辞》应是诉讼文书的原件。文书内容是严令子妻阿白诉丈夫的堂弟严住君多占了她的地,每年还要交两个丁男(此二丁男已经逃走)的租庸,请县里处分。从后面的案卷看,县里接到诉《辞》后命坊正带严住君来县里询问。严住君用《辩》作了回答,说自己没有多占,阿白所少的地,是北庭府史匡君感花了一千文钱从阿白手中买来的,有保人作证。由于文书后残,最后如何判决我们不能详知。此件《辞》的上诉人阿白,应该是一般百姓。若与此《辞》前面残存的另一件董毳头《辞》看,笔记完全不同,知是本人所写,当然也可能是雇人所写,总之,不是由官府出人统一謄清的。
例八,唐景龙三年()张智礼辞
此件《辞》亦为上述案卷中的一件。内容是张智礼向县里申请,请于宽乡天山县补足所欠口分常田和部田。《辞》中没有“标的”,是因为申请人无法指定该得的田地的位置。下令“付司”的“虔□”,是高昌县令张智礼应是普通百姓。
例九、唐开元三年()交河县安乐城万寿果母姜辞
此件《辞》的笔迹极拙劣,可能是拟的草稿,因此“县司”没有另抬头,不符合《辞》的一般格式。“请裁”后面也缺了“谨”字。《辞》的内容不明,上诉人阿姜是个“百姓”。
例十,唐宝应元年()百姓曹没冒辞为康失芬行车伤人事
此件《辞》是《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的一件,内容是曹没冒向县里起诉康失芬驾车将其女儿撞伤一事。县里接到诉《辞》后,命将肇事人带到县里询问,最后判决是“放出勒保辜,仍随牙”。上诉人是天山县百姓,“铮”是天山县令。本件《辞》的字迹朴拙,与前后所存《牒》、《辩》不同,应是本人书写。
通过以上十例,我们可以看出,使用《辞》来上诉或申请的人,基本是百姓(内有妇女二人,即严令子妻阿白和万寿果母阿姜)和卫士。检查其他残存的《辞》,则使用者还有僧人、里正、健儿、兴胡等,都是没有官品的“庶人”。
从内容看,十件中多与田亩纠纷有关(五件),其他四件分别为差兵役、行车撞人、赡养纠纷、请公验,余一件内容不明。查阅其他残存的《辞》,所诉内容还包括因病请白丁充侍、请从兄男充继子、举取练绢纠纷、番期舛误、勘查鞍具并辔、受雇上烽、租佃纠纷、因病不堪行军、赔死马并呈印、查找失踪兄弟、请颁发市券、请改给过所等,其中有些不是诉讼,只是申请,可见《辞》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私人上行文书,其中诉讼用者可称为诉《辞》,申请用者可称为申《辞》。
从格式看,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一、“年月日姓名辞”置于《辞》的首行,这与下面要说的《牒》以及《辩》不同。二、姓名前要写明籍贯如某乡人或身份如百姓、卫士等。这与《辩》明显不同。后者不必写籍贯、身份(保辩除外),但一定要写年龄。这可能是因为《辞》是最初的法律文件,看重的是身份;《辩》是面对官府询问的回答,身份已知,故需强调未知的年龄。三、一定要有受理机构如县司等,这与下面要说的《牒》不同。四、最后以“谨辞”结尾。区别《辞》、《牒》的重要标识,即一为“谨辞”结尾,一为“谨牒”或“牒”结尾。
至于为何《辞》要将年月日姓名置于首行,而《牒》则否,目前还不能很好解释。我的初步想法是:诉讼文书中,诉讼人非常重要,须承担真实起诉、诉辞真实的责任,必须首先让官府知道,因此列在首行。宋元以后的诉讼文书,首列告状人,也是这个道理。而《牒》演化自官文书,但省略了收发信机构,造成首行无发信人即诉讼人的状况。也正因如此,《辞》的形式为以后的诉讼文书所继承,而《牒》的形式则被此后的诉讼文书淘汰了。
四、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牒》
如上节所说,唐代诉讼文书最基本的形式是“辞牒”。《辞》是一般庶人所用,《牒》则为“有品已上”者使用。
关于《牒》,相关研究甚多。国内方面,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是比较早的综合研究。文中分牒式文书为平行型、补牒型、牒上型和牒下型四种,特别强调主典之“牒”,“仅仅是‘判案’环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把它和原始的牒文区分开来,当然也不妨仍然称它为牒”。这后一个结论很重要,日本学者的意见即与此不同。日本方面,前引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专设一节研究《敦煌發見の公式令規定文書》之《牒》,认为敦煌文献中最多的公文书是牒式文书;牒和状一样,是公私均广泛使用的文书;并复原了祠部牒的样式、列举了一件首尾完整的敦煌县向括逃御史上的牒。中村又在《吐魯番出土の公式令規定文書》之《牒》中指出有品者对官府使用的文书称《牒》;吐鲁番出土的牒式文书数量很多;并列举了五个例子。文中着力分析了“谨牒”和“故牒”的区别,但没有区分不同样式的《牒》,所举5例中大部分属于公文书。最近,赤木崇敏发表了《唐代前半期的地方公文体制———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的长文,文中将牒式文书分为两类:牒式A与牒式B,并认为前述卢向前所说的一类牒实为《状》(详后)。他所归纳的两类牒式的格式如下:
牒式A
发件单位件名(为……事)
收件单位(正文)……牒至准状(式)
故牒(或谨牒)
年月日
府
某曹参军事史
牒式B
发件单位牒收件单位
件名
牒……(正文)……谨牒
年月日发件者牒
以上列举的中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文书的《牒》的研究上,对于私文书的《牒》,特别是用作诉讼文书的《牒》着力不多。本文即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一下诉讼文书的《牒》的格式、使用者及其内容。吐鲁番文书中确实有很多《牒》,但如果我们接受赤木崇敏的意见,其中有许多就不是《牒》而是《状》了。这一问题我们下节讨论,这里仅列举比较典型的《牒》。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为诉讼文书的《牒》的格式,与赤木所说的牒式B很近似,但由于是私人用文书,所以没有所谓“发件单位”与“收件单位”。没有“发件单位”很好理解,因为是私人行为;但没有“收件单位”,即没有如《辞》中所列的“县司”等受理机构,就不太好理解了。
与《辞》一样,我们先将完整的诉讼文书的《牒》的格式整理如下:
标的(所诉人或物)
牒:所诉内容。结尾———谨以牒陈,请裁(或“请乞判命”、“请追勘当”、“请处分”等),谨牒。
年月日籍贯身份姓名牒
例一,唐永徽元年()严慈仁牒为转租田亩请给公文事
此件《牒》是上诉人严慈仁为将租来的田转租给安横延,而安横延要求出具公文,因此申请发给公文。严慈仁为云骑尉,是正七品上的勋官,所以用《牒》不用《辞》。请注意,此件《牒》即没有写受理机构,其年月日和姓名置于最末行。
例二,唐开耀二年()宁戎驿长康才艺牒为请处分欠番驿丁事
此为康才艺“于州陈诉”的《牒》,内容是汇报应该上三番的驿丁,只上了两番,请处分。“驿长”在唐代没有品级,但属于可免课役的、有一定权力的职役(或称色役)。或者这样身份的上诉人也用《牒》。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即此《牒》属于一件公文书,是官府(驿)上于官府(州)的《牒》。
例三,唐□伏威牒为请勘问前送帛练使男事
此《牒》某伏威上诉,说王伯岁的儿子偷看他们全家乘凉。从“水窗”字样看,他们全家可能在沐浴(洗凉水澡)。由于王伯岁的儿子是官员子弟,因此提起上诉。由于文书残缺,不知上牒的年月以及“某伏威”的身份。文书行言其为“曹主”,但唐代并无“曹主”这一职官,推测是某种低级官吏的俗称。无论如何,他应是官吏,所以使用了《牒》。
例四,武周载初元年()史玄政牒为请处分替纳逋悬事
此《牒》是史玄政说自己租的地,欠了去年的“地子”,而所欠“地子”应由去年租此地的索拾力交纳。史玄政是里正,曾署名为“前官。由于未见他曾担任其他职官的记録,因此或许这里的“前官”即指里正,也就是说,当地人将“里正”视为“官”。无论如何,史玄政与一般庶人不同,上诉使用了《牒》。文书最后没有年月日和署名,不知是否因阙文之故。
例五,武周久视二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上柱国康万善牒为以男代赴役事
此件《牒》出自敦煌,内容是康万善因年老患病,申请由其子替他充任马军。可能因为是上诉人诉自己的事,所以前面没有目标(也可能前面有缺文)。康万善是上柱国,正二品勋官,所以使用了《牒》。从其籍贯只署“悬泉乡”看,上诉所至机构应该是县一级。
例六,唐景龙三年()品子张大敏牒
此件《牒》与上节《辞》中的例七、例八同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是其中的一件原件。《牒》的内容是申请退还“不生苗子”的劣地,要求授予好地。申诉人张大敏是品子,虽非官吏,但也不同于一般庶人,因此使用的是《牒》而非《辞》。
例七,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
此件《牒》连在瓜州所发过所后,是原件,内容是石染典因要去伊州,请允许持此过所继续前往。行的印以及“琛示”上的印均为“沙州之印”,行的印为“伊州之印”。因此,此《牒》所上当为沙州,“琛”当为沙州刺史或都督,过所在伊州已经使用完毕。申请人石染典是游击将军,为从五品下武散官,所以使用的是《牒》,而同样申请过所的“甘州张掖县人薛光泚”用的就是《辞》。不过要注意的是,石染典虽是游击将军,但署名时仍称“百姓”,作“百姓游击将军”云云,故知当时署名为“某县某乡人”,一定是庶人;署名“百姓”则可能是庶人也可能有某种身份。
例八,唐开元二十二年()杨景璇牒为父赤亭镇将杨嘉麟职田出租请给公验事
此《牒》是杨景璇因其父的职田先后租与多人,恐互有差错,申请县里提供公证(公验)。其父杨嘉麟是镇押官,代行镇将事。镇将,若是下镇镇将的话,是正七品下。杨景璇不知是否有品级,总之不是一般庶人,所以使用了《牒》。下令“付司”的“宾”,据考证是张待宾,时为西州都督或刺史。如此,则此《牒》虽向县申请给公验,但直接递到州里。或是因为“镇”直接由州(或都督府)管辖。
例九,唐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
此件《牒》与上节《辞》例十,同属《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内容也是起诉靳嗔奴家人行车将自己的孩子撞伤。虽然两件诉讼文书起诉内容相同,但前例用的是《辞》,本例用的是《牒》,原因不明。两个起诉人署名都是“百姓”,或许本件“百姓史拂郍”与《牒》例七之“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类似,虽名“百姓”实际是一个有品级或有身份的前任官吏。
例十,唐大历三年()曹忠敏牒为请免差充子弟事
此《牒》是曹忠敏因残疾(手无四指),加上年老,申请免去差充子弟。申诉人身份为“百姓”,但使用了《牒》。或许到唐后期,《辞》的使用减少,《牒》的使用增多、泛化了。
以上与《辞》相仿,也举了十个例子。从这十个例子看,使用《牒》作为诉讼或申请文书的有云骑尉、驿长、曹主、里正、上柱国、品子、游击将军、镇将男等,均非一般庶人(白丁)。从残存的其他《牒》看,还有前仓督、别将赏绯鱼袋、前镇副、流外等。开元以后,一些“百姓”也开始使用《牒》,如例九、例十。还有“百姓尼”。这些“百姓”使用《牒》,或者是因为他们另有如“游击将军”等身份,或者是因为开元以后《牒》的使用泛化造成的。
从内容看,以上十例涉及田亩租赁、违番欠番(这个可能是官方行为)、偷看就凉、兵役替代、田租(地子)纠纷、田亩授受、职田租赁、驾车伤人、申请免役、请给过所等,从其他《牒》的例子看,还有买马付主、请给市券、患病归贯、异地请禄、申请墓夫等。这些内容主要是民事纠纷而无刑事诉讼。为何没有刑事诉讼文书的《牒》(以及《辞》)留存呢?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从格式看,《牒》与《辞》的不同是:一、申诉人的籍贯、身份、姓名及年、月、日置于末行。二、起首写“牒”字,但并无受理机构如县司、州司等。三、结尾写“谨牒”。为何有这种不同,也是应该继续研究的重要问题。《牒》中间还有一大类,其特点是以“牒,件状如前,谨牒”结束。赤木崇敏等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格式的《牒》实为《状》。我们将其与《状》一并讨论。
五、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唐代诉讼文书中的《状》
《状》在诉讼文书中占有重要位置,所谓“诉状”、“告状”等,都与《状》有直接关系。但是如前所述,《状》又并非法典规定的诉讼文书名称,因此,《状》在唐代究竟有何意义,它与《辞》、《牒》的关系如何,它是一种独立的诉讼文书吗?这就成了很难回答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点初步探讨。
关于《状》的研究更多。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唐代使用广泛的官文书,而且因为它与书仪相关,又是使用广泛的上奏和书信文书。中村裕一在前引《唐代公文书研究》第三章《敦煌發現の公式令規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三小节《状》中,认为状与表类似,是个人书简之一,公私皆用,“对状的用途不可能予以定义”。文中列举了五代时的两个状,特别指出有的状是以“状上”起首,而以“牒”结句,即存在着以“牒”结句的状。他又指出,认为这些以“牒”结句的文书是“状”,是后人的判断,后人的判断则未必正确。作者又在第五章《吐鲁番出土の公式令规定文书》第二节《上行文书》第三小节《状》中认为在敦煌没有唐代的状的留存,但在吐鲁番文书中有。文中重申了写有“件状如前”的牒应是《状》,并指出:在上申文书中,何时使用状,何时使用牒,有无规律性,是今后应该探讨的问题。
赤木崇敏继承了中村裕一的看法,以《石林燕语》为依据,明确指出写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的文书是《状》,并给出了状式文书的样式:
发件单位状上收件单位
件名
右……(正文)……谨(今)録状(以)上(言)。
牒,件状如前。谨牒。年月日发件者牒。
关于《状》的最新研究还有吴丽娱()《试论“状”在唐朝中央行政体系中的应用与传递》。文章探讨的主要是作为公文书的奏状、申状在中央行政体系中的运用。作者()又有《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地方机构行用的状》一文,列举了众多例证,认为状和牒由于中转的原因产生混用,即用牒的方式将“状”的内容递交。到晚唐五代,虽不需递交而可以直接申上,但保留了“牒件状如前,谨牒”的格式,它实际上是状。文章还以“县”的申状为例,给出了申状的标准格式。此文结论虽与赤木的文章略同,但精深过之,对其变化背后原因的探讨更是很有说服力。
不过吴丽娱文章()虽然涉及个人用“状”,但与赤木文章一样,主要探讨的是地方机构行用的状,也没有专门研究诉讼文书。那么,作为私人诉讼用文书,有没有《状》呢?那些写有“牒,件状如前,谨牒”的诉讼文书是如吴丽娱或赤木所说那样的《状》吗?首先要说明,在唐代法典中的“状”,如前所述,主要是“事状”、“情状”、“罪状”之意。所谓“具状申诉”之中的“状”有些或应作此解。吐鲁番文书中的“状”有些或即此义。例如一件诉讼文书《辞》的范本:
此处的“以状咨陈”,在下面另一件《辞》的范本中,写作“以状具陈”。两处“状”都是“事状”、“情状”之意。再一例:
《唐上元二年()府曹孝通牒为文峻赐勋事》的最后三行为:
此件为《牒》无疑,且是下行的《牒》,所以用了“故牒”而非“谨牒”。其中的“状”也是“事状”、“情状”,意思是“今以事状牒告与你,牒至后按照牒的内容行事”。
因此在唐前期,牒文中所谓“件状如前”中的“状”大致多为此意。“件状如前”与“件检如前”、“件勘如前”、“检案连如前”一样,都是主管案件的官员处理完案件后,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词句,“状”应该是动词。这其中“件”的含义,按照司马光《书仪》此件为《牒》无疑,且是下行的《牒》,所以用了“故牒”而非“谨牒”。其中的“状”也是“事状”、“情状”,意思是“今以事状牒告与你,牒至后按照牒的内容行事”。因此在唐前期,牒文中所谓“件状如前”中的“状”大致多为此意。“件状如前”与“件检如前”、“件勘如前”、“检案连如前”一样,都是主管案件的官员处理完案件后,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词句,“状”应该是动词。这其中“件”的含义,按照司马光《书仪》的解释,为“多件”的意思。他在列举“牒式”时说:“牒(云云,若前列数事,则云:牒件如前云云)谨牒。”单独一件,就只说“状如前”、“检如前”、“勘如前”,意思是“事状复述(或呈报)如前”、“翻检案卷(结果)如前”、“核查案件(结果)如前”等等。举一个例子:
唐永淳元年()坊正赵思艺牒为堪当失盗事
第10行所缺的字应是“牒”。由于此《牒》只是一件事,所以不必说“牒,件状如前”,而只要说“牒,状如前”即可。《牒》的内容是某坊正赵思艺接到上级要求(奉判)并按照其中内容(准状)核查僧香家被盗事,最后将调查后的事状言上,再写套话“牒,状如前,谨牒”。
此例当属官文书。从其他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现“牒,件状如前,谨牒”(包括“牒,件检如前”等)字样的文书中,最后署名的必定是处理此案卷的官吏,如府、史、典、録事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卢向前的意见,即这种类型的文书在唐前期是判案中的一个环节,虽与原始的《牒》不同,但还应该算是《牒》,而不是状(只有到了唐后期,这种《牒》纔具有了《状》的性质,详下)。前述吴丽娱文()认为前期存在一个用“牒”将“状”中转的过程,但是这件文书是坊正赵思艺自己上的牒,不存在中转问题,但仍使用了“状如前”的词句,可见这里的“状”当为动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附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的《牒》,由于大多与处理案卷有关,属于公文书,因此实际并不在我们探讨的诉讼文书的范围内。
不过,由于“状”除了“事状”、“情状”、“罪状”的含义外,它本身也是一种文书形式,因此出现在文书中的“状”,渐渐与《辞》和《牒》有了某种程度的混淆。《辞》和《牒》有时也被称为状。于是出现了“辞状”(“右得上件□等辞状”)、“牒状”(“右得上件牒状”)等称呼。到《宝应元年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中,如前所述,两个被撞伤的百姓,起诉书一个用的是《辞》,一个用的是《牒》,但到官府询问当事人时,变成“问:得史拂郍等状称:上件儿女并在门前坐,乃被靳嗔奴扶车人辗损”云云,《辞》和《牒》都成了《状》。可见这时,“状”的用法已经泛化,可以代指《辞》和《牒》了。
不仅如此,在一些“牒,件状如前”类《牒》文书中,逐渐在结尾出现了“请处分”、“请裁”等申请处分字样,甚至出现了“谨状”、“状上”。这就使这类《牒》超出了转述事状、汇报检案结果等事务的功能,标志着《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诉讼文书开始出现。
于是《牒》和《状》开始混淆。一件《天宝年间事目历》有如下记载:“兵李惟贵状为患请□茣茱萸等药”、“兵袁昌运牒为患请药。”同样是兵,同样是因患病请药,一个用《牒》,一个用《状》,可见二者已经混淆不清了。
到唐晚期,随着这种个人使用的、写有“状上”、“请处分(请裁)”之类字样的《牒》文出现,《状》作为一种诉讼文书正式出现了。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此类《状》的实例,主要出现在敦煌。这是因为敦煌文书主要是唐后期五代的文书,而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前期的文书。所以一般来说,吐鲁番文书中有《辞》而《状》少见,敦煌文书中无《辞》而有《状》。
这种主要出自敦煌的诉讼文书的《状》,其格式大致如下:
身份姓名状
右(直接写所诉内容)。结尾———伏请处分(或伏请判命处分、伏请公凭裁下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月日身份姓名牒
举一个例子:
此件《状》的内容是诉田亩纠纷。申诉者是押衙兼侍御史。要注意,其身份虽是押衙,但仍自称“百姓”。这或可解释我们在《牒》一节中困惑的现象,即为何有的百姓使用了“有品”者才能使用的《牒》。现在看来,一些低级胥吏(估计是前任胥吏)自称为“百姓”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称“百姓”者中,有些实际是或曾经是官吏。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中还收有多件此类诉讼文书的《状》,可参看。
从这类《状》的格式,可知有这样几个显着特点:1、身份姓名既置于首行,又置于末行,即既同于《辞》又同于《牒》,是混合了辞牒格式的格式。2、没有专门的“标的”,而是直接叙述所诉事项,这实际是吸收了官文书处理案卷的《牒》的格式的结果。“牒,件状如前,谨牒”也说明了这一点。以上两点可证明诉讼文书的《状》是从《辞》《牒》发展而来的。3、《敦煌社会经济文献释录》中所录的几件诉讼文书的《状》,都不是向某机构申诉,而是请求官员个人处分,如本件的“常侍”,以及其他各件的“大夫阿郎”、“殿下”、“司空”、“仆射阿郎”、“司徒阿郎”等。因此颇怀疑这类《状》的格式是敦煌地区特有的。
总之,唐末诉讼文书中的这种《状》,因带有“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应该说属于诉讼文书的《状》的初步形成阶段,带有《辞》《牒》的浓厚色彩。而且,正像中村裕一所说,虽然这种文书因有“状”或“状上”等字样,因此我们称其为“状”,但这是我们现在的称呼,也许当时人仍然称其为《牒》呢。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诉讼文书的“状式”就没有了“牒,件状如前,谨牒”字样,但仍然前列告状人,后以“谨状”(或“具状上告某官,伏乞……”)结束,年月日后复有告状人姓名并“状”字。元代黑水城文书中的诉讼文书,也是前写“告状人某某”,后写“伏乞……”,年月日后再写告状人姓名并“状”字。它们与唐代诉讼文书中《状》的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
六、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
如上所述,从法典用语及出土文书的实例看,诉讼文书在唐代的称呼、形式、格式有多种,且互有交叉,复有演变。大致说来,正规的称呼应该是《辞》和《牒》,同时,其内容常被称为“状”并与实体的《状》逐渐混同,出现了“辞状”、“牒状”等称呼。到唐后半期,作为诉讼文书的《状》开始出现。此时的《状》带有鲜明的《辞》《牒》特点。
与以上状况相适应,在唐代史籍(法典之外)中,对诉讼文书的称呼也很不固定,大致说来,有以下称呼。
1、辞牒
“辞牒”在史籍中使用不多,主要即出现在南北朝至唐代的史籍中。例如有:
《文苑英华》卷三六一引杨夔《公狱辨》云:“缙绅先生牧于东郡,?属吏有公于狱者。某适次于座,承间咨其所以为公之道。先生曰:吾毎窥辞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牍,无不了吾意,亦可谓尽其公矣。”杨夔不同意缙绅先生的说法,此当别论,其中提到的“辞牒”,显然是诉讼文书。
《白居易集笺校》卷二二《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回忆他在苏杭当刺史时事说:“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善恶有惩劝,刚柔无吐茹。两衙少辞牒,四境稀书疏。俗以劳俫安,政因闲暇着”。看来苏杭地区诉讼较少,这里的“辞牒”也指诉讼文书。
2、辞状(附词状)
“辞状”似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以后直至《大清会典则例》都有使用,但最集中的,出现在唐五代史籍中。例如有: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引韦嗣立反对刑法滥酷所上的《疏》,在说到酷吏锻炼冤狱时说“虽陛下仁慈哀念,恤狱缓死,及览辞状,便已周密,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寛舍,其如法何?于是小乃身诛,大则族灭,相缘共坐者,不可胜言”。其中的“辞状”应指诉讼文书或案卷。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言裴怀古为监察御史,“时恒州鹿泉寺僧净满为弟子所谋,宻画女人居高楼,仍作净满引弓而射之,藏于经笥。已而诣阙上言僧咒诅,大逆不道。则天命怀古按问诛之。怀古究其辞状,释浄满以闻,则天大怒”。这其中的“辞状”显然指诉讼文书。
《资治通鉴》卷二百高宗显庆四年()四月条言许敬宗等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颇有疑惑,向许敬宗询问。许敬宗在回答了长孙无忌谋反的原因后说“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这里的“辞状”指诉讼文书。《册府元龟》卷三三九《宰辅部·忌害》记此句为“臣参验辞伏,并相符合,请即收捕,凖法破家”。其中的“辞伏”或当为“辞状”之误。
《册府元龟》卷六一七《刑法部·正直》记“王正雅,文宗时为大理卿。?宋申赐事起,狱自内出,无支证可验。当是时,王守澄之威权,郑注之势在庭,虽宰相已下,无能以显言辨其事者。惟正雅与京兆尹崔管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验其辞状以闻。由是狱稍辩,以管与正雅挺然申理也”。这里的“辞状”与“告事者”相连,也指诉讼文书。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言:“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这里的“辞状”与“诉讼”相连,显然指诉讼文书。
“辞状”又有写作“词状”者。即以上条关于御史风闻的例子而言,《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作:“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将《通典》中的“辞状”写作“词状”。
《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总条)云:“疏议曰:‘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鍜炼成罪。故注云,谓故増减情状足以动事者,若闻知国家将有恩赦,而故论决囚罪及示导教令,而使词状乖异。称‘之类’者,或虽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动;或非示导,而恐喝改词。情状既多,故云‘之类’”。
《旧唐书》卷百九十中《李邕传》记李邕天宝年间为北海太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绩马一匹,及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郎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
唐代以后,“辞状”多写作“词状”。宋代政书《宋会要辑稿·刑法》就有多处“词状”,例如《禁约门》宋徽宗宣和五年()中书省言“乡村陈过词状,未论所诉事理如何”、“或因对证,勾追人户到县,与词状分日引受”。元代政书《元典章》在《刑部》卷十五《书状》“籍记吏书状”、“词状不许口传言语”、“站官不得接受词状”等条中也都明确使用了“词状”。不知上述三例唐代史籍中的“词状”是唐代史籍的原文呢还是后代刊本的改写,从宋元时代固定使用了“词状”看,改写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3、牒状
“牒状”的使用极少,检索《四库全书》,只有17处:最早出自《魏书》,最晚到宋金时期。唐代史籍中的两处,均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其中一处出自《少林寺准敕改正赐田牒》,是少林寺方面回答有关机构对他们“翻城归国”的质疑,说他们曾发牒给当时“翻城”带头者的刘翁重、李昌运,结果李昌运的回答“与(刘)翁重牒状扶同”。这里的“牒状”实际指刘翁重的答辞,与诉讼文书关系不大,但仍然是诉讼过程中的一种证词文书。
4、诉状
“诉状”的使用少于“辞状”而多于“牒状”,有66卷、74处。始于《宋书》,使用直至明清,而以宋朝最多。唐代史籍大约只有二、三处。例如:
《册府元龟》卷四五七《台省部·总序》言知匦使始末云:“唐太后垂拱元年置,以逹寃滞。天寳九载改为献纳,干元元年复名知匦。尝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每日暮进内,向晨出之”。这里的“诉状”显然指诉讼文书,不过《册府元龟》此处的《总序》是宋人所作,不能确证这是唐人的称呼。
《册府元龟》卷四九一《邦计部·蠲复》记元和六年十月关于放免租税制曰:“又属霖雨所损转多,有妨农收,虑致劳扰,其诸县勘覆有未毕处,宜令所司据元诉状,便与破损,不必更令捡覆;其未经申诉者,亦宜与类例处分”。这里的“诉状”与下列“申诉者”相关,指诉讼文书无疑。
《续玄怪录》卷二《张质》讲亳州临涣县尉张质被追到阴间,“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门,,门额题曰‘地府’。入府,经西有门,题曰‘推院’。吏士甚众,门人曰:‘临涣尉张质。’遂入。见一美须髯衣绯人,据案而坐,责曰:‘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质被捽抢地,叫曰:‘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未尝推事’。又曰:‘案牍分明,诉人不远,府命追勘,仍敢诋欺’。取枷枷之。质又曰:‘诉人既近,请与相见’。曰:‘召寃人来’。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视质曰:‘此人年少,非推某者’。仍敕録库检猗氏张质,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又检诉状被屈抑事。又牒阴道亳州,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并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年五十一,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替人猗氏张质,年四十七。检状过,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审勘。错行文牒,追扰平人,闻于上司,岂斯容易。本典决于下:改追正身,其张尉任归’”。这里的“诉状”与“诉人”相联系,所指必为诉讼文书。
唐代史籍中关于诉讼文书的称呼肯定还有许多,我们只列举了四种,即“辞牒”、“辞状”、“牒状”、“诉状”,从中可见称呼的不固定。但若细细分析,这四种称呼又各有不同:“辞牒”和“牒状”用例都很少;“诉状”似只出现在唐代后半期;使用最多的是“辞状”。因此,虽然我们说唐代当时对诉讼文书没有统一的称呼,但大致而言,多用“辞状”,后来逐渐演变为“诉状”。这种称呼的变化,与《辞》《牒》逐渐演变为《状》是相一致的。
七、简短的简论
以上我们通过一些实例,介绍和分析了唐代诉讼文书中的《辞》、《牒》、《状》,以及唐代史籍中对诉讼文书的相关称呼,由此可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诉讼文书在唐代法典上的称呼是“辞牒”。就实际使用看,在唐前期,普通庶民使用《辞》;有品级或有一定身份的人使用《牒》。《辞》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及“辞”置于首行,且有受理官司的名称,最后有“请裁,谨辞”类套话。《牒》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置于末行,没有受理官司的名称。在“标的”之下以“牒”起首,结尾有“请裁,谨牒”字样,最后在姓名下复有“牒”字。《辞》和《牒》的内容都可以称为“状”,是“事状”“情状”“罪状”之意,后来受实体文书的《状》的影响,逐渐出现了“辞状”“牒状”类称呼,诉讼文书中也开始出现“状上”、“请处分,谨状”类字样,后来出现了个人使用的诉讼文书的《状》。这种《状》含有《辞》和《牒》的特点:庶民和官员都可以用;姓名置于首行(此似《辞》),年月日姓名复置于末行(此似《牒》);前多有“状上”(此似《辞》),后有“请处分,谨状(或请裁下)”,最后有“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似《牒》)。当《状》逐渐出现后,《辞》就变得少见了,《牒》也逐渐被淘汰(因其首行不列诉讼人或告状人)。这可以说是《状》吸收了《辞》《牒》的特点,从而使用广泛化所造成的结果,影响直至后代。
唐朝人对诉讼文书多称其为“辞状”(或许是因为行文需要,即因四六文等行文节奏的缘故,需要将“辞”之类文字变成双字节,于是添加了“状”字)或“词状”,到后期,渐有“诉状”的称呼产生。此后,“状”就成了诉讼文书的固定称呼。在宋代,史籍多称“词状”和“诉状”,元代亦然。这就与唐代的《辞》和《状》有了很明显的继承关系。除此之外,称“辞牒”或其他的也还有一些,大约都不占主要地位,换句话说,《辞》《牒》作为诉讼文书曾经的形式或称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我们今天叙述唐代诉讼文书,或以诉讼文书来研究各种问题,应该如何称呼呢?我想,叫“辞状”“诉状”都可以,而前者或更具唐朝特色。
关于唐代诉讼文书的实况,以上只是作了极其粗浅的介绍和分析,若要得出更符合唐朝实际的结论,可能还需要再搜集更多的文书资料和传世史籍资料,这一工作,希望在今后能继续进行下去。
文章来源:《敦煌吐鲁番研究》年01期
编排:此生慕东坡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tulufanzx.com/tlfszx/11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