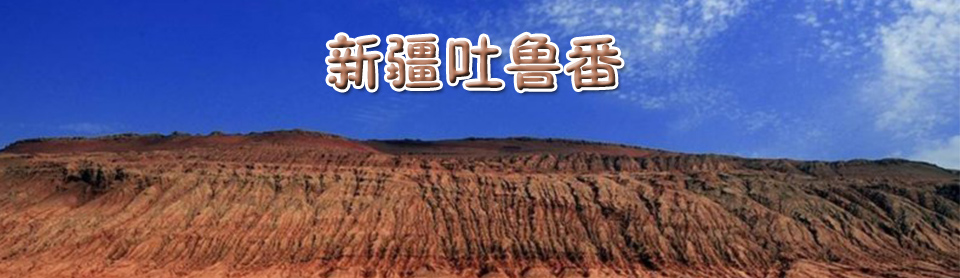南行的脚步吐鲁番一
年10月
早晨六点多就起来,收拾好,一切停当,八点多出发。走时女儿叮嘱我把衣服穿厚点,很暖心的臭宝贝,爸爸爱你。每次出远门,我都习惯穿那件黄色的衣服,算不算是个怪癖?我喜欢紫色,紫色黄色互补,至少觉得可以让自己心里舒服点吧。
下楼时,滴了几滴雨,还想的“早雨不断,一天的啰嗦”,可太阳没有理会天气预报,依旧灿烂的露出笑脸。没到昌吉,我就迷糊睡着了。
从昌吉上了高速,绕过乌鲁木齐市区,一路顺畅。在达坂城稍作停留,不见王洛宾先生歌曲里美丽的姑娘。只是去上厕所,那个瘦小的穿制服的中年人,让我到他们工作人员用的厕所了。贴心的扶我上了台阶,很感动。本想买点达坂城的特产大豆吃,看拥挤的人群,想想还是算了吧。
过小草湖安检,乘客要刷身份证。去年五一去阿克苏,被这里的警察以检查后座的安全带为由,罚款二十元。这次还好,挥手过了。可是再向前走,车却堵的厉害。原来是在修路,加之国庆大假,出来玩的人多。走走停停,蜗牛般爬行。
车窗外,就是荒凉的戈壁滩,远处的山上也不见一丁点儿的绿。林立的巨大风车,有的转的欢,有的偷懒一动不动,大约是和所对的风向有关吧。戈壁滩上肆虐的风,卷起阵阵弥漫的黄沙,久久不能散去。
本来一直睡着的张天天小朋友醒来了,对车窗外最初看到的挖掘机已然毫无兴趣,不停的喊着回家。直到他妈妈实在哄不住一声怒喝,他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的看着窗外,安静的看着,不再说话。接下来的几千公里路,孩子可是受罪了啊!为了生活而奔波,孩子离不开,只有一起奔波了。
堵车时,总有加塞的,穿插的,想尽一切办法往前走,哪怕是多一步。往往走来走去,他还在你的边上,或者后面。何必?终于不挤了,一路狂奔。这大约堵了一个多小时,车流如泄洪口的闸水,急速的拉开距离。
吐鲁番,终于是要到了。路两旁,已可见大片大片的葡萄架。葡萄是没有了,大都是挂在了晾房,酿成了葡萄干。晾房是吐鲁番的特有建筑,用土坯砌成,四壁有眼通风,利用自然风烘干葡萄里的水份,终成葡萄干。
本地维吾尔族老乡基本都是很富裕,这是得利于地缘优势,又有哪个地方的葡萄比得上吐鲁番的葡萄?吐鲁番地处南北疆咽喉要道,丝绸之路必经之路。自古商贾云集,历史积淀浑厚,新疆的历史几乎都凝聚在吐鲁番。楼兰不是梦,交河故城亦是真。
吐鲁番看起来不大,高楼不见多少。民房总是可以看到隐约的伊斯兰风格,老屋子,院墙,总是砌成各式花样,不忽略每一处表现美的地方。
大街小巷,走着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女人,帅气的维吾尔族男人,民族与时尚相融。与周遭汉族老百姓,外地游客,国外游客,汇成一条和谐的人流,缤纷着这座古老的城市。
梅姐接我们,到了家里,一顿地道的新疆拉条子吃过,勇子他们一家三口就继续赶路去往成都,一路顺风吧!之后我睡了一觉,头挨着枕头就睡去,睡得极沉,极是香甜,家的感觉。
三号,鹏自北京归来,杀羊,大锅煮肉,大串烤肉,就在坎儿井边一个维族老乡的老院子,这种感觉一定很美。
梅姐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和油门上车。油门柱银色双拐,梅姐带着两个伤兵出门。门口遇一维族大叔:“欧呦,这个地方咋这么多这样的人?”我和油门相视莞尔。
出租车到了坎儿井,车费21.5元。梅姐给维吾尔族师傅22元。那个师父说五毛的没有,梅姐说那就一块给我,五毛我的有给你。师父旋即找回五毛,尴尬一笑。简单的对话,有幽默的。
曹明胯下一辆绿色电动三轮车来了,让我坐他边上,副驾!来到院子。院子里的树长的很茂盛,葡萄架下放了一张巨大的木板床。在三颗环抱的老榆树间,有一个地洞。看到一个戴着头巾的维族大嫂蹲着洗碗。一时没明白,这是什么风俗?在坑里洗碗?问了油门才知道,这是地地道道的“坎儿井”。
维族大嫂看有生人,起身上了台阶,我微笑点头问好,她也略显羞涩的微笑,用不太熟练的汉语说你好后,转身离开。台阶七八层,我不太方便下,可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这应该是当地居民的生命之源吧。酷热的高温,地表水极易蒸发。这留存在地下的坎儿井,就这样走家串户,融入了这里人的骨血。
梅姐拿来了刀斧,切、旋、砍、剁,肢解了一只羊。温柔善良能干的大姐,是油门的幸福!曹明和油门去接了鹏,兄弟间无需多言,一个眼神的交流就够了。简单寒暄后,觉得腿有些僵硬,就起来走走。去了院子后面上了个厕所,慢慢走到了大门外。
“吐鲁番市凯萨民间文物博物馆”,这是什么地方?看红色高大的门敞开着,木板大门底部的漆有些剥落。门楼顶,砌着晾房。大门侧显著位置贴着免费参观的字样,我信步走入。
院内放两张巨大的床,上面铺着鲜艳的民族地毯。一个美丽的维吾尔族少妇笑吟吟的坐在床上,我说我可以坐坐吗?还问她懂不懂汉语。她微笑点头说可以。大床对面有一个写着“入口”的门洞,左侧有一个挂着艾得来丝绸的门。一个八九岁的小巴郎带我进来,顺手打开了一盏灯。
进去,我被震到了!这是一个很简陋的展厅,土墙,砖地。墙上挂着最古老的马鞭,清朝,民国时的衣服,马灯,手工制作的多头灯架,各种马靴,男人穿的女人穿的马靴,袜子。尖头的,带跟的,皮子的,毡做的。还有纸币,清朝,民国,新中国发行的各类票:布票,肉票,油票……各种形态的壶:油壶,水壶,拳头大的,半人高的,陶制的,铜制的……一对流星锤,黑色的圆球上呲着尖利的三角刺,用精致的链子连到一起。当时使用这种武器的,一定是个武林高手。或许这刺上,不定沾着马贼或者土匪的血吧。
展厅是用指头粗的钢筋焊成框,然后用铁丝编织。走过一间,小巴郎就会灭了后面的灯,打开前面的灯。问他,他只是懂一点点,说是爸爸懂的多。西面门口两个展柜,写着“手机卖场”,估计是哪个手机店淘汰的柜子。
展厅出来有个院子,院子里放着稍微大点的物品。有叉,有耙,有石磨,有推车,有木门木窗。木窗都是漂亮的回形菱形等各种花纹,都是纯手工打造。还有一个棉花取籽机,完全手工制作,显示了本地先民卓越的智慧,和高超的手工制作工艺。
木制马槽,铡刀,地毯印花模具……我无法一一累叙,这里,就是一本新疆民俗文化活动的活字典!
坐在宽大的床上,我终于等来了凯萨儿大哥。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肚子大大的,眼神里有着几乎不属于这个年纪少有的干净,又有一丝疲倦。我们笑着紧紧握着手,那一瞬间,心意似乎已经想通。
大哥五十六岁,已经退休。最初是做生意的,和文物多少有关。却由买卖,变成了收集。他说要把这些东西保存!“有些东西,不是钱能够代替,需要保留,需要继承。”大哥说的时候,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动。我也被感动!
大哥的院子靠近坎儿井风情园,周围全是做生意的。这个占地三四百平米的院子,若是经营农家乐,就以十一这几天的游客数量,一天收入几千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哥家里五个孩子,两个孩子在国外上大学,一个四年级,一个一年级,一个还没上学。经济压力很大,之所以坚持开这样一个免费参观的博物馆,是为了什么?
“民族间的交流碰撞,文化间的交流碰撞,有时就是这样一件件小小的民俗文物,留着,可以教育后代。钱,买不来一些东西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样有几人?
凯萨儿大哥的院子里热闹起来,好多人都会好奇的问:看看不要钱吗?得到肯定,参观完了都聚在我们两个周围。几个东北的游客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加上东北人特能侃,我们就一起聊了。
凯萨儿大哥不善言辞,加之汉语也不是特别的流利,我就主动接招了。我问他们了解新疆的历史吗?对吐鲁番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去了中国好多省市,看过许多名胜古迹,很自得的样子。却不谈我问的问题,
我想他们大约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告诉他们楼兰的消失,交河故城的存在,坎儿井工程的巨大,以及院子里这些古老的民俗物件,所能代表的新疆维汉及其他民族战天斗地的勇气和智慧。
突然发现自己有导游的潜质,其实我知道,这是源于我对历史的喜爱和崇敬,和对新疆的热爱。凯萨儿大哥从屋子里抱出了一个大西瓜,他美丽的妻子手脚麻利的切开,让这些客人吃。可他们好像有些犹豫,我想他们多少还是担心什么,或者是不了解新疆人的好客与热情。
我先拿了一块,好甜的西瓜!这里白天高温,昼夜较大的温差,让产自于此的水果,聚集了较大的糖分,所以吃起格外的甜。
我把自己当成了主人,拿起西瓜让东北的客人吃。他们不再犹豫,边吃边啧啧称甜。凯萨儿还给我们看世界上最小的葡萄,一粒粒如绿豆般大小,如晶莹剔透的红玛瑙。
好多人问可以吃吗?我想应该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是不忍心吃的,这简直就是大自然所凝结的完美的艺术品。许多新疆本地的游客也是称奇,不停的拍照。有位大姐,拿在手里对着阳光看,真像是在看珍贵的宝石。
客人一批一批的来走,凯萨儿大哥却只是陪我说话。他说他曾经想让政府资助,可一直得不到答复。他也想把这里搞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了解新疆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生活。
大哥的眼睛里始终淡然却又坚定,我却能看到大哥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闪动。是啊,内地人对新疆的误会太深,大哥的心里是委屈的。如大哥所说,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坏人,破坏了新疆的安定和谐,他们绝对代替不了新疆所有的人。
我也觉得鼻子发酸,谁不渴望安稳?谁又愿意被误会?我想,大哥绝不是一己之力,还有千万个和他一样的新疆儿女在努力。
我诚恳的告诉大哥,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只是想尽我的一份绵薄之力。我叫过来他可爱的女儿,她羞涩的笑。我给了她一百块钱,告诉她要努力学习,买书看,多看书。
凯萨儿大哥美丽的妻子急了,不让女儿拿,他也急了,要把钱还给我。我告诉他们,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想和他们一起努力,虽然我的能力有限。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诚的。我不曾忘记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也想尽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虽然很少,虽然用物质的方式表达。
小女孩对我不停的说谢谢,我紧紧的抱抱她。我相信,美丽的新疆是真诚的,美丽的新疆人是善良的,热情的,宽广的!这是我们新疆独有的地域性格,如同我们新疆的大漠戈壁,绿洲胡杨,亘古的天山,永远不会改变。
李鹏在喊我开饭了,我告别他们一家,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拉过手就是朋友,我想我还会来的,一定!
大床上,放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大煮羊肉,凉面,烤肉,自家地里种的小白菜……色彩鲜艳,香味扑鼻。李鹏问曹明:我们喝点撒?“坎儿井里水满满的不够喝嘛?”我们哈哈大笑。
曹明有个比较经典的幽默笑话,华子曾经问他,吐鲁番埋沙的疗效如何?他说“人嘛,抬上来的,跑上回去的”。酒是白粮液,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产的。一起的还有这个院子的主人,两个维吾尔族老乡。他们在介绍自己时,说是“花儿”一样的朋友。他们的脸上绽放着真诚的笑,真像是盛开的花朵。第一次觉得脸上的皱纹如此好看。
我不能喝酒,只是一小杯。我的脸上也抑制不住的笑,听他们说,听他们开怀大笑。背景音乐就是挨着院子的“坎儿井乐园”里,传来的欢快鼓点,动人的维吾尔族民乐旋律。
阳光透过葡萄架,撒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为什么不开怀大笑?生活,是有这样那样的坎坷,是有这样那样的不顺,可我们总不能停滞不前。微笑,大笑,是可以释怀许多的。
我没有去过美国,可听人说,八十年代的美国人脸上,一副从没被人欺负过的样子。我生于七零后,想想,八十年代的我身边的人们,总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脸有菜色,面色木然少了许多生气。到了九零年代,有了喜色,眼神里充满了希望,直至现在,却看有如填不满的沟壑——欲望的沟壑,深不见底的沟壑。
吐鲁番人,整个是微笑的。永远一副开心满足的样子,都是“花儿”一样的朋友。梅姐脸上,总挂着沉静而善良的笑,嘴角微微上扬。晚上总会给我和油门端来烫烫的水泡脚,就李鹏耍赖有时不洗脸。
早晨我们还香甜的睡在透过窗户玻璃温暖的阳光里,梅姐就起来做好早饭喊我们起床。有时是白米粥,有时是牛奶。炒一个热菜,拌一个凉菜。花卷,馕饼。简单却又爽口。油门话不太多,白白净净,眉清目秀的。因为腿伤,偶尔有些小消沉,却也能骑着电动车挎着银色单枪(拐杖)上班。
花花个子不高,皮肤白皙,有异国风情的漂亮。她的眼睛会勾人的,顾盼之间,溢彩动人。性格也是极开朗活波,一口流利的维语听起来别有韵味。
她和“花儿”一样的维族朋友用维语交流,我虽然一句都听不懂,可看他们交流间,手在有节奏前后左右上下挥动,时而握拳时而张开五指时而指点江山般。还配合脸部丰富的表情,眉眼间的飞舞灵动,非常有感染力,只是看他们说话就极是有趣。
兵兵大个子,真诚而又幽默,那种语言中夹杂的诚挚的幽默。听了后不得不笑,开心的笑。他们的周围都是各族人民,最多的是维吾尔族。这里的维吾尔族老乡,是有一种“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活在当下”的境界!
兵兵说,以前夏天嘛,树林带里,草坪上,到处都躺满喝醉的巴郎子。他们从村里来到城里,烤包子吃给,烤肉吃给,抓饭吃给,炒面拌面吃给,白酒喝给,啤酒喝给。然后嘛,舞跳给。最后嘛,家嘛回不去了树林里睡给,草坪上睡给。
有次当地政府为了整顿市容市貌,把树林里草坪上等等各种醉鬼抬出来,整整齐齐的摆了一排。内个场面嘛,太壮观了!想想,你都会忍俊不禁的笑。他们都难得放假,可却专门抽出时间陪我们。今天就计划去“苏公塔”,是兵兵带我们去。梅姐有事,油门就被我们拽着一起去了。
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四周都是平房居多。几乎每家院落都有一间晾房,屋顶一般都放有一巨大的床,说巨大是豪不夸张的。兵兵说新城的一家有十二个娃娃,每天睡觉前,都要数数头,看够不够。十二个娃娃加两口子,十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大不大?
有一天睡到半夜,下雨了。吐鲁番下场雨很难得的,两口子就急急慌慌的把孩子一个个往屋子里抱。黑漆嘛胡的,就顺手把床上铺的毯子卷起来扛到了屋子里。第二天起来,怎么数都少一个娃,到处都找不到。郁闷之余,就想的先把昨晚淋湿的毯子拿出来晒晒吧。结果毯子打开,丢掉的娃娃卷在毯子里。我们哈哈大笑,这就是兵兵的幽默。
不觉中,来到了苏公塔。李鹏去找合适的角度去写生,兵兵和油门在车里聊天,我就独自一人去了。依旧免票,我走入这座几百年的院子。
先是来到额敏和卓的雕塑前,他身材魁梧,右手高举经书,双目炯炯直视前方。边上有一块横放的长方形石碑,记载着苏公塔修建的历史背景等等。
苏公塔是新疆境内现存最大的古塔,建成于公元年,迄今已有年的历史,它是清朝时期维吾尔族著名爱国人士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为了恭报清王朝的恩遇,表达自己对真主的虔诚,并使自己一生的业绩流芳后世,而自出白银两建造。
苏公塔又名额敏塔,之所以称作苏公塔,完全是因为该塔由额敏郡主的儿子苏莱曼建造完成,故得名于此。当地又称其为“忠孝塔”,忠于朝廷,孝于父辈。
我向塔走去。塔前有一个圆形小广场,四周有两层台阶,应该是坐人的。我步履蹒跚,慢慢坐在台阶上,看着高高屹立于灰色天空下的塔,又不禁发呆。
一群外国游客走过,有个戴眼镜的姑娘向我招招手,微笑。我也向她微笑点头,她大约是把我当成了虔诚的信徒:一个人走路如此困难,都要来朝拜,值得钦佩。亦或是因为,看我发呆的眼神里充满了敬仰之情吧。
对历史,我总是心怀敬仰,发自内心的。塔身下粗,三分之二的部位开始收小,塔顶为圆形,典型的伊斯兰教风格。塔基建在一宽大的台子上,塔左侧是一处连接的方形建筑。高大的拱形尖顶门,套着一个小许多的同样形状的门框,镶着两扇黑色的长方形木门。
最顶端,是并排七个同样形状的小窗。土黄色的墙体,没有刷任何东西,就是黄土本身的颜色。我爬台阶是不方便的,左右两侧有供我等身体不便的人上的便道,有扶手。
我从左侧上,亦步亦趋,走走,我就要抬头看看。终于来到塔前,天也晴了。塔,似乎有了光泽。我缓步向前,把脸,轻轻的贴在塔身,有温暖的感觉。我仰望,塔直指苍穹,像是变得遥不可及,融入了蔚蓝色的天空……绕着塔,抚摸一块块砖。一块块砖,叠堆成菱形、方形、三角形等纹样,浑然一体。
南侧,却看到向下延伸的裂纹。后人出于保护,用铁条箍了几道。这里地震很少发生,周边到处都是葡萄地。可能是因为开垦灌溉,导致地层发生了变化。
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对于它们的保护,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有些东西,一旦倒了,重新再建,已不是原来了。丢了,就是丢了,再也不会找回来。
塔南侧,是一块墓地。墓的形状,是能分出男女的。穆斯林说,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他们死后无任何陪葬。“活在当下吧!”真主可能如是说!留下的,只是这一座座如精巧艺术品的坟,任世人围观,听风吹鸟鸣……你活着带来了什么?你留下了什么?一冢坟一粒尘沙吧……
我没有进入那扇门,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不知道那里曾经有着怎样的历史,贸然进入,是对历史的亵渎,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我甚至至始至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
或者是为了给下一次来找个理由吧,回头再看看,我想这里我还会来的。
作者:士君年生于新疆芳草湖五场,喜好爬格子,笔耕不辍,坚持梦想,以文字创造世间种种美好。
长按
转载请注明:http://www.tulufanzx.com/tlfszx/67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