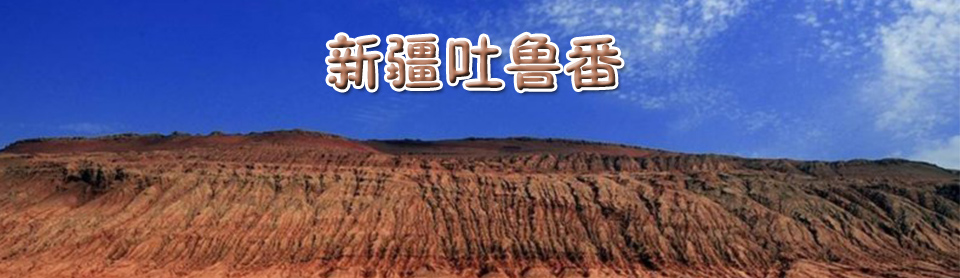學術論文宗教信仰王素吐魯番出土功
王素
本文原載《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年,第11~35頁。感謝王素先生授權推送!
魏晉南北朝迄唐初,人們爲求死後享受,常在墓中隨葬衣物和記載這些衣物的所謂《衣物疏》。這種《衣物疏》,因詳記死者隨葬衣物,不僅成爲研究當時日常生活的絶好素材,也成爲現代考古驗收發掘品的絶好憑據,而頗爲學術界所重。大約唐高宗以後,這種《衣物疏》,由於一直附記死者對冥世的追求,隨着這種追求的提高,而逐漸向《功德疏》演變。這種由《衣物疏》演變成的《功德疏》,因詳記死者崇佛功德,不僅仍爲研究當時日常生活的絶好素材,又爲研究當時宗教信仰的絶好資料。池田温[1]、馬雍[2]、小田義久[3]、白須浄真[4]、Seidel[5]、鄭學檬[6]、侯燦[7]、孟憲實[8]、劉昭瑞[9]、鍾國發[10]、荒川正晴[11]、劉安志[12]、町田隆吉[13]等先生,先後都對《衣物疏》或《功德疏》進行過研究。其中,就《功德疏》而言,白須浄真、小田義久、池田温、町田隆吉等先生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重视。而小田義久先生對於《功德疏》中反映庶民浄土信仰的《隨願往生經》的研究更能給人以啓發[14]。我在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的過程中[15],對唐西州(即今吐魯番地區)前期的五件《功德疏》曾作初步探討,現將有關庶民浄土信仰的心得,分二部分記録如下,敬請方家指正。
壹資料篇
第一件爲《唐乾封二年(年)西州高昌縣前官氾延仕妻董真英功德疏》,全文14行,每行後部多有殘損,兹按原格式釋録如下:
1維大唐乾封二年,歲次丁卯,□□□(十一月)
2丁丑朔,十八日甲戌。西州高昌□□□(縣人前)
3官太吏氾延仕妻董氏□□(真英),□□(持佛)
4五戒,不違五行,算□□□□□
5計與生死之道不同。伏□□□□
6各本歸屬,但爲□□□□
7朱書爲證。
8爲正信佛弟子清信女真英,疴疾□□□□
9心講法華經一部。寫法華一部,灌頂經一□(部),
10金剛般若廣略兩卷,消伏、觀音各一卷。及□(誦)□(灌)
11頂經百○五遍,法華一百廿五遍,智度论一□(遍),□□(金剛)
12般若波羅蜜經四遍,涅槃經一□(遍)
13七度總布施三伯餘僧。誦觀□□(音經)□□□,□□
14經一千遍。至十一月十八日未□□(時卒)。□□□□
15所作福業,具注如前。
這件《功德疏》,出自斯坦因所編阿斯塔那第9區第2號墓[16],亦即現編阿斯塔那號墓。上記乾封二年十一月朔爲丁丑,與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記同年同月朔爲丁巳不同。該墓另出《唐乾封二年(年)氾延仕妻董真英墓誌》一方[17],上記同月十八日干支爲壬辰,與疏及同書記同日干支爲甲戌亦異。説明疏及墓誌均有舛誤。但二者記董真英出身事迹基本相同。綜合二者,我們得知:墓主董真英,西州高昌縣人,前官氾延仕之妻。生前崇信佛教。乾封二年九月上旬染病,十一月十八日卒,時年五十有一。同年十二月四日葬。這件《功德疏》爲墓主董真英葬前所寫。
這件《功德疏》分前後二部分:前七行爲前部分,記董真英出身事迹;後七行爲後部分,記董真英崇佛功德。前部分以上已作介紹,以下專門介紹後部分。
按後部分記董真英崇佛功德,大致分講經、寫經、誦經、布施四類:
講經指演講佛經。僅一種,爲法華經。此經全名爲《妙法蓮華經》,凡七卷二十八品,主要爲天臺宗所信奉。但其中第十五、十六、十八等品,記佛與彌勒問答,宣説指歸浄土;第二十五品,記佛爲無盡意菩薩解説觀世音的名號因緣和稱名作用,觀世音菩薩開周遍法門普度衆生事迹,以及三十三應普門示現等功德,又爲浄土宗的彌勒門派和觀音門派所重視。
寫經指抄寫佛經。共五種,爲法華經、灌頂經、金剛般若廣略、消伏經、觀音經。法華經見上。灌頂經全名爲《佛説灌頂經》,自三歸五戒,至生死得度,凡十二卷。雖屬密宗經典,但因宣説受戒修行,頗爲浄土宗所信奉。金剛般若廣略,H.Maspero謂即智儼撰《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略疏》。按智儼爲華嚴宗二祖,擅長義疏之學,著作多達二十餘部,此略疏(二卷)爲其中之一。但智儼卒於總章元年(年),亦即墓主董真英卒後一年。智儼在世時,其著作已流傳至西州,并被當地優婆抄寫作功德,似乎太過神速。因而H.Maspero之説未可盡信。只能斷定,所謂金剛般若廣略,應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一種疏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即著名的《金剛經》。此經僅一卷,記佛在舍衛國爲須菩提等説空慧事,爲重視無我境界的佛門宗派所信奉。消伏經全名爲《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一卷,記佛爲月蓋長者請觀世音菩薩救療毘舍離國惡病事,爲浄土宗觀音門派所信奉。觀音經全名爲《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即前述《妙法蓮華經》之第二十五品,爲浄土宗觀音門派的最重要經典。
誦經指背誦佛經。共四種,爲灌頂經、法華經、涅槃經、觀音經。灌頂,法華、觀音三經見上。涅槃經全名爲《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屬大乘五大部經之一,主要宣説如來常住,涅槃常樂,衆生悉有佛性,爲浄土宗所信奉。
布施共七次,僅知涉及三百餘僧,是錢是物不詳。
第二件爲《唐咸亨三年(年)新婦爲阿公録在生功德疏》,全文94行,前若干行中後部稍有殘損,兹按原格式釋録如下:
1謹啓:阿公生存在日,所修功德,應□□□。但從
2去年染患已來,所作功德,具如右件:
3一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請廿僧乞誦,并施馬一疋
4與佛。將黃紬綾袍裙一領(下殘)
5懺悔出罪。
6一今年正月一日,請十僧轉
7至月七日了。於此日更請五十僧乞誦,并施
8佛銀槃一,重廿兩。當日罪懺悔。
9一至正月八日後,更請十僧轉
10到正月十八日了。計轉大般若了。
11一昨正月十三日,復請屈尼僧廿人乞誦,出罪懺悔,
12一阿兄在安西日,已燒香發心,請佛生禪師讀
13一千遍金剛般若經,起被
14日設齋供養,并誦雜經六懺悔。
15一復於安西悲田寺佛堂南壁衆人出八十
16疋帛練,畫維摩、文殊等菩薩變一捕(鋪)。又
17發心爲阿公修造,願知。
18一復至二月七日,更請十個尼僧出罪。
19一當未亡時,二月七日夜,阿公發心將家中七斛大
20百師一口,施彌勒佛玄覺寺常住。請百僧乞誦,
21并誦二僧七日行道,并造卌九尺五色幡一口。至八
22日齋後,即依阿公本願,屈
23衆布施大像、常住百師,并請洛通法師出罪
24懺悔。因此亦即屈請通法師受菩薩戒,亦懺
25悔,願知。
26一至八日,大衆散後,即請孟禪師子
27發心行道,旦暮二時懺悔。當日夜即將
28阿公裌綾袴一腰,布施二行道
29阿公乃即捨化。當時即依隨願往生經文造
30作黃幡懸著刹上,并旦暮兩時燃卌九燈,請
31僧兩時懺悔,并屈三僧使經聲
32經。阿公合得合得十方浄
33一阿公昨日發心造卌九尺神幡,昨始造成,初七齋
34日慶度,願知。
35一昨日因行次到塔中,見門扇後阿公手記處,云
36讀涅槃經計欠兩遍半百卷。昨初十日,屈典坐
37張禪師讀半遍廿卷了,并請轉讀妙法蓮華
38經一部,金光明經一部,設一七
39僧復轉讀涅槃經—遍卌卷了,并出罪懺悔。
40一昨從初七後,還屈二僧轉讀,經聲不絶,亦二時燃
41燈懺悔。至今月廿一日,復更請卌僧,更轉讀涅槃
42經卌卷一遍了。計前後總讀涅槃經囗遍半囗卷
43了。
44一今日因轉讀涅槃經,更將後件物等施三寶:
45馬一疋布施佛鞍轡一具施法
46黃綢綿袍—領絲巾子一枚
47黃布衫一領羅纀頭一枚
48帛布衫一領帛綢綾半臂一腰
49生絁長袖一腰熟銅挍腰帶一
50沉香霸(把)刀子金口一鞊靴一量並氈
51兩色綾接一帛練裌袴一腰
52帛練單袴—腰帛練汗衫一領
53帛練褌一腰細絲襪一量
54墨緑紬綾裙—腰紫黃羅間陌複—腰
55緋羅帔子一領紫紬綾襖子一錦褾
56五色繡鞋一量墨緑紬綾襪一量錦
57右前件物布施見前大衆
58紫綾裌裙—腰緑綾裌帔子二領
59肉色綾裌衫子一領
60右件上物新婦爲阿公布施
61一右件物今二月廿一日對衆布施三寶,亦願知。
62一阿公患日,將綿一屯布施孟禪師,請爲
63諸天轉讀今(金)光明經,亦請知。
64諮阿公生存在日功德,審思量記録,但命
65過已後功德具件如前,願將此文簿
66前頭分雪,須覓生天浄佛國土,不得求人
67間果報。在生産業、田園、宅舍、妻子、男女、
68奴婢等物,並是虛花,皆無真實。
69阿公每讀經思義,應審知之。直爲生死
70道殊,恐阿公心有顛倒,既臨終受
71戒,功德復多,假使在中蔭中,須發上心覓
72好生處,不得心有戀看,致落下道。
73謹録此簿,分强分疏。出離三界,求勝上界。
74若得生路,托夢令知。
(原空二行)
75開相起咸亨三年四月十五日,遣家人祀德
76向冢間窟底作佛,至其月十八日,計成佛
77一萬二千五百卌佛。日作佛二百六十元,々廿佛。
78於後更向窟門裏北畔新塔廳上佛堂中
79東壁上,泥素(塑)彌勒上生變,並菩薩、侍者、
80天神等一捕(鋪),亦請記録。
81往前於楊法師房内造一廳並堂宇,供養
82玄覺寺常住三寶。
83又已前將園中渠上一○木布施百尺彌勒。
84又已前家中抄寫涅槃經一部,注子法華經一部,
85注子金剛般若經一部,對法論經一部;更於後寫
86法華經一部,大般若經一帙十卷。作(昨)更於生絹畫兩
87捕(鋪)釋迦牟尼變,並侍者、諸天。每年趙法師請
88百僧七日設供,阿公每年常助施兩僧供,并
89施物兩丈,恒常不絶。
90又昨阿公亡後,即常屈三僧轉讀,供養
91不絶。又更爲阿公從身亡日,々畫佛一軀,
92至卌九日,擬成卌九軀佛。又今日請一僧就門
93禮一千五百佛名一遍。以前中間阿公更
94有修功德處,亦不具記,願自思量申雪。
這件《功德疏》,出自阿斯塔那29號墓(文書七,66~74頁;圖文叄,~頁)。該墓爲男女合葬墓,男屍先葬。此疏應爲男屍亦即所謂“阿公”的隨葬物。但此“阿公”卒葬於何時,疏中并未明確記録。疏中明確記録時間僅一次,即所謂“開相起咸亨三年四月十五日”。小田義久先生據此認爲,此疏所記,爲“阿公”生前的咸亨二年(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死後的咸亨三年(年)四月十八日間的功德。但此處“開相”,據下文,似指在窟内開造佛像和泥塑變相。如然,則此明確記録,是此“阿公”開始開造佛像和泥塑變相的時間。其他場合,則均稱“去年”“今年”,以及含義模糊的“昨(日)”“今(日)”。其中,“今年”二月八日條記功德畢,接云:“阿公乃即捨化。”推知“阿公”卒於“今年”二月八日。至於葬於何時,卻仍無法得知。
這件《功德疏》據原安排似分前後二部分:前74行爲前部分,後20行爲後部分。但實際上并不可分。因爲前74行爲正文,後20行爲補充,内容并無太大區别。譬如:開篇雖云僅記“阿公生存在日所修功德”,包括“去年染患已來所作功德”,但實際上還記“(阿公)命過已後,(新婦爲阿公所作)功德”。“阿公”生前生後所作功德,前後二部分均曾記録。因此,以下擬不分前後,僅據類别加以介紹。
按全疏記“阿公”崇佛功德,大致可分誦經、讀經、轉經、寫經、設供、布施、造幡、造像、行道、禮佛名、塑畫變相等十一類:
誦經五次,未詳何經。第一次在去年十二月廿三日,係“請廿僧乞誦”。第二次在今年正月七日,“請五十僧乞誦”。第三次在今年正月十三日,“請屈尼僧廿人乞誦”。第四次在前次稍後,係“誦雜經”。第五次在今年二月七日夜,“請百僧乞誦”。按:此五字下,原接云:“并誦二僧七日行道。”其中“誦”應爲“請”之誤。因而不作誦經之例。又,今年二月七日條,記“更請十個尼僧”下缺;同月八日條,記“并屈三僧使經聲”下缺,疑亦屬誦經。
讀經一般指真讀佛經。二次,爲金剛般若經和涅槃經。第一次在今年正月十三日後、二月七日前,新婦阿兄在安西(龜兹)日“請佛生禪師讀一千遍金剛般若經”。金剛般若經見前。第二次在今年二月初十日,所謂“阿公”手記謂“讀涅槃經計欠兩遍半百卷”,遂於“昨初十日,屈典坐張禪師讀半遍廿卷了”。涅槃經亦見前。該經四十卷,讀兩遍半正好百卷,讀半遍也正好廿卷。
轉經一般指假讀佛經。即唯讀每卷之前中後數行。由於翻轉經卷迅速,稱爲轉經,又稱爲轉讀。七次,爲大般若、妙法蓮華、金光明、涅槃等經。第一次在今年正月一日,“請十僧轉”。第二次在今年正月八日後,“更請十僧轉”。據接云“到正月十八日了,計轉大般若了”,知此二次所轉均爲大般若經。按大般若經全名爲《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内容廣博,爲諸部“般若”集大成之名作,一般佛門宗派均信奉。其中“嚴浄佛土品”(初會第七十二)宣傳浄土思想,尤爲浄土宗所欣賞。但因部大卷多,難以全部誦讀,多作轉經之用。第三次在今年二月初十日,“請(典坐張禪師)轉讀妙法蓮華經一部、金光明經一部”;又請僧“轉讀涅槃經一遍卌卷了”。妙法蓮華經見前。此金光明經應爲北涼曇無讖所譯之四卷十九品《金光明經》(唐義浄所譯之十卷三十一品《金光明最勝王經》,此時似乎尚未開始翻譯),記如來法身(金)、般若(光),解脫(明)三德,一般佛門宗派均信奉。第四次從今年二月初七至廿一日,初七日請二僧,至廿一日請四十僧,仍“轉讀涅槃經”,前後共轉讀若干遍若干卷。第五次在“今日”,似即寫此《功德疏》之日,亦“轉讀涅槃經”。還有二次:一次在“阿公”患日,亦“請(孟禪師)爲諸天轉讀金光明經”;一次在“阿公”亡後,“常屈三僧轉讀”,未詳何經。
寫經二次:以前曾寫涅槃經一部、注子(即小字注)法華經一部、注子金剛般若經一部、對法論經一部;以後又寫法華經一部、大般若經一帙十卷。按對法論經大概即《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原文衍一“經”字。此論十六卷,爲南印度羅羅國安慧菩薩雜糅、唐僧玄奘奉詔譯出,專門解釋《阿毘達磨集論》。“阿毘達磨”意爲大法、無比法,也就是智慧。其説將趨向涅槃法的聖道稱爲“對法”。此論不僅爲大乘瑜伽學系立説之典據,亦爲浄土等佛門宗派信奉之要籍。
設供指設齋供養。因事設供二次:第一次在今年正月十三日後、二月七日前,請佛生禪師讀經,每日“設齋供養”。第二次在“阿公”亡後,常屈三僧轉讀時,“供養不絶”。又經常設供二樁:第一樁是以前爲楊法師造廳堂,遂常“供養玄覺寺常住三寶”。第二樁是“每年趙法師請百僧七日設供,阿公每年常助施兩僧供”。
布施在佛教中有三義:一財施,二法施,三無畏施。此處指第一義,亦即財施。“阿公”生前亡後,向佛施舍財物,次數、種類均甚繁多,疏文具在,這裏不擬排比細舉。總之,動物(馬)、植物(木)、紡織品(巾帔、衣衫、袴褌、袍裙、鞋襪)、金屬製品(銀槃)等,幾乎無所不包。由此亦可見此“阿公”家庭富裕,財力充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二月七日夜,“阿公發心將家中七斛大百師一口,施彌勒佛玄覺寺常住”。大百師爲容器名。玄覺寺供奉彌勒佛,應屬浄土宗彌勒門派寺院。
造幡三次:第一次在今年二月七日夜,“造卌九尺五色幡一口”。第二次在今年二月八日,時“阿公”剛死,“即依隨願往生經文造作黃幡懸著刹上”。按:隨願往生經原爲前述密宗《佛説灌頂經》之第十一卷,全名爲《佛説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浄土經》,主要爲浄土宗所信奉。關於此經,下文還擬詳細評述,這裏不多介紹。第三次在“昨日”,亦“造卌九尺神幡”。
造像一次,在咸亨三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間,於冢間窟底,“計成佛一萬二千五百卌佛”。但這裏有一個問題。即小字接注,稱“日作佛二百六十元,々廿佛”,每日作佛五千二百,四日應作佛二萬八百,與此一萬二千五百卌佛數目不合。是筆誤,或是另有原因,已無法詳考。
行道一次,在今年二月七日夜,係“誦(請)二僧七日行道”。次日(八日)“發心行道,旦暮二時懺悔”,并“布施二行道僧”,應是前次的繼續。行道爲禮佛的一種儀式,即合掌由佛像右方旋轉繞行。
禮佛名一次,在今日,係“請一僧就門禮一千五百佛名一遍”。禮佛名爲浄土宗修行内容之一種,即背誦佛名。
塑畫變相三次。第一次在今年正月十三日後、二月七日前,新婦阿兄於安西(龜兹)悲田寺佛堂南壁,“衆人出八十疋帛練,畫維摩、文殊等菩薩變一鋪”。第二次在咸亨三年四月十八日稍後,於窟門裏北畔新塔佛堂東壁,“泥塑彌勒上生變,並菩薩、侍者,天神一鋪”。第三次在前次稍後,“更於生絹畫兩鋪釋迦牟尼變,並侍者、諸天”。
此外,還有燒香、受戒、燃燈、畫佛、造廳堂等功德。
第三件爲《唐咸亨四年(年)左憧憙生前功德及隨身錢物疏》,全文10行,中數行後部稍有殘損,兹按原格式釋録如下:
1憧憙身在之日告佛:
2憧憙身在之日,十年已前,造壹佛、貳陪(菩)
3薩。逕三年,説汙(盂)蘭貪(盆)逕(經)。左郎身自□
4伍伯僧表銀錢用。左郎隨身去日,將
5白銀錢參斗,白練壹萬段,清(青)科(稞)、□麥、粟、
6等伍萬石。婢阿迦、婢□香、婢多不脛、婢解、奴雙
7德、婢尾香。咸亨四年四月廿九日付曹主左□
8校收取錢財及練、伍榖、麥、粟等斗斛收
9領取用,鎧(?)有於人,不得拽取。付主左
10憧憙收領。
這件《功德疏》,出自阿斯塔那4號墓(文書六,~頁;圖文叄,頁)。該墓另出《唐咸亨四年(年)左憧憙墓誌》一方,上記左憧憙爲西州高昌縣人,卒於咸亨四年五月廿二日,時年五十有七,但葬日不詳。疏中所記,均爲左憧憙生前功德。該墓又出各類契約文書二十二件,據此,知左憧憙爲高昌縣崇化鄉一高利貸者,家庭殷富[18]。
這件《功德疏》分二部分:一部分記功德,一部分記隨身錢物。既不是純粹的《衣物疏》,也不是純粹的《功德疏》,具有前者向後者過渡階段特徵。這裏不談隨身錢物,只談功德。
按這件《功德疏》記左憧憙所作功德,僅造像、説經,布施三類。造像僅造一佛、二菩薩。説經應即前面的講經,僅講説盂蘭盆經。布施也僅限於布給五百僧銀錢。按盂蘭盆經全名爲《佛説盂蘭盆經》。“盂蘭”意爲“救倒懸”。“盂蘭盆”用置百味五果,供養佛僧,希望借佛僧的恩光,解脫餓鬼倒懸之苦。此經即説“盂蘭盆”的緣起及修“救倒懸”之法,頗爲浄土等佛門宗派所信奉[19]。
第四件爲《唐咸亨五年(年)爲阿婆録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牒》,全文16行,首尾完整,兹按原格式釋録如下:
1右阿婆生存及亡没所修功德件録條
2目如左:
3一文軌法師邊講法華一部。敬道禪師邊受戒。
4一寫涅槃經一部,隨願往生經一卷,
5觀世音經一卷。
6一延僧設供誦大波若一十遍。
7一自省已來,口誦餘經,未曾懈廢。
8一延法師曇真往南平講金光明經一遍,
9法華兩遍,金光波若一遍。
10一在生好喜布施,乍計不周。
11右告阿婆從亡已後,延僧誦隨願往生,
12至今經聲不絶。并誦大波若一遍。
13葬日布施衆僧銀錢叄伯文。
14牒件録在生及亡没所修功德條目如
15前,謹牒。
16咸亨五年三月廿二日牒
這件《功德牒》,出自阿斯塔那號墓(文書六,~頁;圖文叄,頁)。該墓另出《唐咸亨五年(年)張君行母墓誌》一方,上記校尉張君行母爲南平人,咸亨五年三月十二日卒,同月廿二日葬,時年九十有餘。按:南平舊爲高昌城名,唐降爲鄉名,屬西州天山縣[20]。張君行母原爲南平人,出嫁從夫定居高昌,因而卒葬高昌城東之阿斯塔那古墓區。據此,知牒中“阿婆”乃張君行母,“”即張君行本人。按大谷文書亦見張君行其人,凡二條:一爲《唐顯慶四年(年)張君行租田契》(號),其中張君行官爲“租田人隊正”;一爲《唐天授二年(年)西州高昌縣佃人文書》(號),其中張君行僅爲高昌縣寧昌鄉“佃人”。牒及墓誌年代,在此二條之間,張君行官爲“校尉”。“隊正”(領60人)、“校尉”(領人)均爲折衝府官,由“隊正”陞“校尉”順理成章。此後雖僅爲“佃人”,但在當時的西州,“佃人”的身分不低,因而小田義久先生推測此三者應爲同一人,頗有道理。張君行曾出仕爲官,家庭經濟應該不錯。
這件《功德牒》據編排分前後二部分:前部分記在生所修功德,後部分記亡没所修功德。但這裏僅按類别加以介紹。
按全疏記張君行母所修功德,大致可分講經、寫經、誦經、布施四類:
講經二次,均在生前。第一次係請文軌法師“講法華一部”。第二次則請曇真法師“往南平講金光明經一遍,法華兩遍,金光波若一遍”。其中金光波若應即前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小田義久先生認爲第二次講經爲何要往“南平”理由不明。筆者以爲應與張君行母原爲“南平”人有關。
寫經一次,亦在生前,爲涅槃經一部,隨願往生經一卷,觀世音經一卷。其中觀世音經即前述《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誦經三次。第一次在生前,係請僧“誦大波若一十遍”。第二次在前次稍後,係親自“口誦餘經”,且一直“未曾懈廢”。第三次在卒後,係請僧“誦隨願往生”,并“誦大波若一遍”。其中大波若即前述《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布施據説甚多,但生前“乍計不周”。卒後僅一次,係給“衆僧銀錢三伯文”。
此外,還有受戒、設供等功德。
第五件爲《唐西州高昌縣成默仁誦經功德疏》,全文5行,首尾完整,兹按原格式釋録如下:
1西州高昌縣安西鄉成默仁,前任别
2敕授焉耆都督府録事,去景龍四年二月廿七日,
3制改授沙州壽昌縣令。自記姓已來,每月六齋兼六時續誦
4法花(華)經壹伯遍,金剛般若經壹阡遍,大方廣佛名經壹伯
5遍。諸雜經不成部帙,不記遍數。
這件《功德疏》,出自阿斯塔那號墓(文書七,頁;圖文叄,頁)。該墓未出墓誌,疏中成默仁是否墓主難以斷言。據疏僅知,此成默仁爲西州高昌縣安西鄉人,曾任焉耆都督府録事,景龍四年(年)二月廿七日,改任沙州壽昌縣令。卒葬時間均不詳。按大谷文書亦見成默仁其人,凡二條(號、號),均屬《武周天授二年(年)西州高昌縣佃人文書》,均作該縣安西鄉“佃人”。雖然時間在二十年前,但因人名、鄉名全同,推測此三者應爲同一人。此成默仁以前儘管曾爲“佃人”,但在當時的西州,由於各種原因,“佃人”并不意味身分不高。根據後來仕宦情況看,成默仁家庭經濟也應該不錯。
這件《功德疏》分前後二部分:前二行半爲前部分,記成默仁出身仕歷;後二行半爲後部分,記成默仁崇佛功德。前部分以上已作介紹,以下專門介紹後部分。
按後部分記成默仁崇佛功德,僅齋日、誦經二類:
齋日即所謂“每月六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謂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進齋,爲六齋日。
誦經僅法華、金剛般若、大方廣佛名三經。前後二經各誦一百遍,中一經則誦一千遍。其餘“雜經”當然亦有,但因“不成部帙,不記遍數”。按其中大方廣佛名經未見記載[21],推測并非正式佛經,只是地方寺院爲便於誦讀,而對“佛名”所作的一種彙録。
貳探討篇
通過以上對資料的詮釋,可以認爲,這五件《功德疏》的疏主,多爲浄土宗信徒。但浄土宗門派較多,他們究竟信仰其中哪一門派呢?這就需要瞭解當時浄土宗分門别派的情況。按東晉十六國以來,浄土宗門派雖多,但真正有影響者卻僅有三,即彌勒門派、彌陀門派和觀音門派。
彌勒門派信仰彌勒浄土。彌勒浄土指彌勒佛所居兜率天宫。彌勒梵姓Maitreya,或譯爲慈氏(按稱彌勒爲慈氏有多説,此處僅取其一),故所居兜率天宫又名慈宫。相傳彌勒出身南天竺婆羅門種姓,因將繼承釋迦牟尼佛位,上生兜率天内院,亦即所謂彌勒浄土。信徒死後均可往生兜率天宫,免除輪回,永不退轉。又相傳,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彌勒又將下生,在轉輪聖王所在國土的華林園内龍華樹下成正覺。并將三會説法,初會九十六億人,次會九十四億人,三會九十二億人,一齊獲得所謂“阿羅漢果”。届時世界變得無限美好,没有水火、刀兵、饑饉之災,人壽八萬四千歲,安穩快樂,説之不盡。信徒即使未能往生兜率天宫,在未來世界,亦能無憂無慮,福壽綿長。彌勒信仰之鼓吹,始於東晉釋道安(~年)。《高僧傳》卷五《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傳》云:“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彌勒信仰的修行内容,根據不同情況分爲三等,大致包括修功德、供養、行三昧、讀誦、繫念、稱名、造像、禮拜等。彌勒信仰之經典,最重要的稱爲“彌勒三部”,即:(1)《佛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卷,北涼沮渠京聲譯;(2)《佛説彌勒下生經》,—卷,後秦鳩摩羅什譯;(3)《佛説彌勒大成佛經》,一卷,亦後秦鳩摩羅什譯。彌勒信仰之寺院,供奉所謂“彌勒三尊”,即中爲彌勒佛,左爲法花林菩薩,右爲大妙相菩薩。
彌陀門派信仰彌陀浄士。彌陀浄土指阿彌陀佛所居西方極樂世界。此極樂世界因能“安心養身”,又稱安養世界。或合安養與極樂,并稱安樂世界。而阿彌陀梵名Amita,譯爲無量,因壽命等本亦無量,又稱無量壽佛。相傳該佛原爲一小國國王,後出家,法號法藏。經過漫長時期,累積無限德行,最終成爲十方諸佛中主管西方之佛。西方爲極樂世界,飲食百味,伎樂萬種,有生無死,有樂無苦,種種妙趣,亦説之不盡。信徒死後均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安養心身,穩享福壽。彌陀信仰之鼓吹,始於東晉僧竺法曠(~年)。《高僧傳》卷五《晉於潛青山竺法曠傳》云:“(法曠)每以《法華》爲會三之旨,《無量壽》爲浄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稍後,經釋慧遠(~年)與宗炳、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廬山般若雲台精舍阿彌陀佛像前,建齋立誓,結社念佛,共期往生西方,而逐漸發揚。至唐僧善導(~年)大力宣傳,終於光大。本來,彌陀浄土有報土和化土之異説,或以爲彼土爲報土,凡夫不能往生。或以爲彼土分報土和化土二種:地上菩薩往生報土,凡夫二乘往生化土。善導主張彼土均爲報土,凡夫亦均可入彼報土。這樣,彌陀浄土遂爲老百姓普遍接受。善導又曾總結往生彼土的修行内容,爲讀誦、觀察、禮拜、稱名、讚歎、供養。其中稱名(即念佛,也就是念阿彌陀佛之名)最爲重要。彌陀信仰之經典,最重要的稱爲“彌陀三部”(或“浄土三部”),即:(1)《佛説無量壽經》,二卷,曹魏康僧鎧譯;(2)《佛説觀無量壽經》,一卷,劉宋畺良耶舍譯;(3)《佛説阿彌陀經》,一卷,後秦鳩摩羅什譯。彌陀信仰之寺院,供奉所謂“彌陀三尊”,即中爲阿彌陀佛,左爲觀音菩薩,右爲勢至菩薩。
觀音門派信仰觀音浄土。觀音浄土指觀音菩薩所居天竺南海普陀落迦山。該山花樹繁茂,常有光明,故或譯作光明山、小花樹山。觀音全稱觀世音,避唐太宗諱省稱觀音。又名觀自在。或謂爲阿彌陀弟子,或謂爲阿彌陀化身。又傳阿彌陀涅槃後,將繼位爲佛,號普光功德山王佛,或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常充彌陀浄土接引使者,而普陀落迦山亦成爲通往彌陀浄土的中轉站。觀音信仰流行甚早。《晉書·苻丕載記》云:“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説明早在十六國時期,觀音信仰就已流行。觀音信仰的修行内容,與前述彌勒、彌陀二信仰大同小異。觀音信仰之經典,即前文提到的從《妙法蓮華經》獨立出來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簡稱《觀音經》)。觀音信仰之寺院,主要供奉觀音菩薩。
此外,又有所謂“十方諸佛”門派。該門派信仰“十方浄土”。本來,對於信仰浄土的庶民而言,無論往生哪一門派浄土,都是求之不得的良好歸宿。但彌勒、彌陀、觀音三浄土都非常美好,既難以全部往生,又難以區别選擇。這樣,就出現了包括所有美好的所謂“十方諸佛”和“十方浄土”。該信仰之重要經典,就是前文提到的《隨願往生經》。按:所謂《隨願往生經》,原爲密宗《佛説灌頂經》第十一卷之“普廣品”,故又稱《普廣菩薩經》。相傳爲東晉沙門帛尸梨蜜多羅譯。由於流傳甚廣,名稱繁簡不一。關於這些,小田義久先生已有研究,毋須贅述,《大正大藏經》所收名爲《佛説灌頂隨願住生十方浄土經》。從定名稱“十方浄土”看,已知此經不屬彌勒、彌陀、觀音三浄土,而將自己列爲另一門派。該門派條件優越,自然也頗多信衆。如吐魯番阿斯塔那44號墓出土的《唐殘發願文二》中,提到“先獻十方諸佛”,就指此“十方浄土”(文書六,頁;圖文叄,72頁)。該信仰的修行内容,與前述彌勒、彌陀、觀音三信仰稍有區别。如《隨願往生經》規定死後須懸幡,云:“造作黃幡,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浄土。”規定死後須燃燈,云:“燃燈四十九,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規定死後須轉讀、燒香、詠贊,云:“從父母命終,轉讀尊經,燒香禮拜,歌詠讚歎,無一時廢,竟於三七,經聲不絶。”這種修行内容,似乎更適合庶民。因此,《隨願往生經》雖有僞經之説,且不爲浄土正宗所看重,廣大庶民卻信之不疑。
按古代庶民信仰佛教,除了祈求現世的福壽,便是追求來世的享樂。因而當時庶民有關佛教造像,現世的釋迦除外,便數來世的浄土諸佛爲最多。如葉昌熾《語石》卷五統計北魏佛教造像,謂“以釋迦、彌勒爲最多,其次則定光、藥師、無量壽佛(彌陀)、地藏菩薩,琉璃光,盧舍那、優填王、觀世音”。佐藤智水根據雲岡,龍門、鞏縣諸石窟和所知傳世金銅像的類别數字,統計北朝佛教造像,釋迦尊,觀音尊,彌勒尊,彌陀33尊,其他造像較少[22]。這足以體現庶民對現世和來世的重視。但其中也有一個問題。現世的釋迦這裏暫不討論。來世的浄土三佛,雖然統計數字不一,但很明顯,北朝時期,彌勒、觀音稍佔優勢,與唐以後彌陀獨霸浄土十分不同。轉變的原因相當複雜,這裏也暫不討論[23]。只想指出,儘管從造像看,當時庶民對浄土三佛似乎并未一視同仁,但實際上,他們很難做到只信仰其中哪—佛。因爲,爲了能夠往生浄土,他們一時間對於浄土諸佛恐怕都不敢怠慢。這一點,既與前述有關“十方諸佛”和“十方浄土”的形成背景相符合,又可與吐魯番地區浄土宗的早期信仰形態相印證。
我們知道,在吐魯番地區,浄土宗的誕生與發展,有着十分悠久的歷史。一般認爲,最早曾受西域佛教的影響。西晉佛經翻譯大師、號稱“月支菩薩”和“敦煌菩薩”的西域高僧竺法護,曾譯出“彌陀三部”之一的《佛説無量壽經》(已佚),和“彌勒三部”之一的《佛説觀彌勒菩薩下生經》(即《佛説彌勒下生經》,亦佚)。吐魯番曾出土竺法護譯的《諸佛要集經》殘卷,説明他的譯經曾在吐魯番地區流傳[24]。後秦佛經翻譯巨匠、出身龜兹國的高僧鳩摩羅什,曾譯出“彌陀三部”之一的《佛説阿彌陀經》,以及“彌勒三部”之二的《佛説彌勒下生經》和《佛説彌勒大成佛經》。鳩摩羅什被呂光從龜兹擄到河西,走的是高昌道,也就是今吐魯番地區,他的譯經對吐魯番地區自然曾有影響。後來,北涼宗室安陽侯沮渠京聲,在高昌獲得并譯出“彌勒三部”之一的《佛説觀彌勒菩薩上昇兜率天經》,和作爲觀音信仰最重要經典的《觀世音觀經》(即《觀世音菩薩普門品》)[25]。或以爲可以證明其時浄土宗已在高昌即今吐魯番地區深深紮根并廣爲流傳。
以前曾有這樣一種觀點,即:整個中國的浄土信仰,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意義較廣,到隋唐時期意義變狹[26]。廣義的浄土信仰,指庶民不受門派的約束,可以廣種博收,追求一切善果;狹義的浄土信仰,指庶民要受門派的約束,只能精選細擇,追求一種善果。或者這樣解釋,即:公元7世紀以前,人們只是漠然相信死後可以往生,對於彌勒或彌陀等浄土無所選擇;公元7世紀以後,人們才多選擇彌陀浄土,彌陀浄土才佔據浄土宗的統治地位[27]。但這種觀點只能説大致正確,因爲在吐魯番地區,似乎也有例外,如吐魯番出土沮渠氏北涼流亡政權承平三年(年)《涼王大且渠安周功德碑》,先云:“彌勒菩薩,控一乘以長驅,超二漸而玄詣。”繼云:“雖曰法王,亦賴輔仁,於鑠彌勒,妙識淵鏡。”最後又云:“稽式兜率,經始法館,興因民願,崇不終旦。”[28]始終只談彌勒及其兜率浄土,似乎屬於狹義的浄土信仰[29]。至麴氏王國建昌元年(年)《新興令麴斌芝造像施入記》則云:“願照(昭)武王以下五王之靈,濟愛欲之河,登解脫之岸,優游浄土,常與佛會。又願考妣亡魂,宗眷往魄,皆越三途,遊神囗界,面聖觀(?)音,獲菩提果。”[30]其中“面聖觀音,獲菩提果”,意義雖然較狹,但“優遊浄土,常與佛會”,意義卻又較廣。似乎浄土信仰的意義正處在由狹變廣的關鍵時期。後來,延昌十七年(年)《比丘尼僧願寫涅槃經題記》末云:“七祖亡魂,考妣往識,超升慈宫,誕生養界。”[31]其中“慈宫”指彌勒的兜率天宫,“養界”指彌陀的西方安養世界。彌勒與彌陀並稱,似乎至此才變成廣義的浄土信仰。然則此時已將入隋。隋唐時期,在吐魯番地區,廣義的浄土信仰,是否又能完全變爲狹義的浄土信仰呢?
按吐魯番出土麴氏王國延壽十四年(年)《高昌王女寫維摩詰經題記》(S.號),先云:“見佛聞法,往生浄土。”後云:“等出苦源,同昇妙果。”[32]不提具體門派,似乎也屬於廣義的浄土信仰。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本世紀初,日本大谷探險隊在吐魯番地區考察發掘,發現了唐代以阿彌陀佛爲本尊的彌陀浄土寺院,獲得了唐代寫本“彌陀三部”,其中還有浄土高僧善導寫的《阿彌陀經》[33]。東京靜嘉堂文庫從我國粱素文(玉書)等人手中購買的吐魯番出土唐寫佛經斷片中,也有《觀無量壽經》和《大無量壽經》等彌陀門派經典斷片。另外,還有不少吐魯番出土唐代世俗彌陀浄土文書。如《二樂叢書》和《西域考古圖譜》所收唐代寫本《往生禮贊》,屢稱“往生安樂國”,“頂禮阿彌陀佛”,“至心歸命禮西方阿彌陀佛”,“願法界衆生三業清浄奉持佛教和南西方一切賢聖”。大谷文書號《唐代浄土教徒祈願文》屢稱“南無阿彌陀佛”。等等。這些也都成爲隋唐時期吐魯番地區浄土信仰由廣義變爲狹義的證據。然而,這些證據并不能概括整個隋唐時期吐魯番地區浄土信仰的形態。因爲,這些有關彌陀信仰的寺院、經典和世俗文書,均無明確紀年。唯一有明確紀年的爲唐代宗大曆六年(年)范陽夫人供養的《絹本浄土變相圖》,其銘文爲:“彌陀願供衆生同登彼岸。期詞夷(?):西方有佛號彌陀,衆生念善出娑婆,寶樹花林金殿閣。共命咸同禮省。大曆六年四月十八日慶。夫人范陽囗空我明,一心供養。”[34]據此,只能認爲,在吐魯番地區,似乎直到唐代中期,廣義的浄土信仰才變爲狹義的浄土信仰。彌陀浄土成爲浄土宗最主要門派,似乎也是唐代中期以後的事。但在唐代前期,或者説在麴氏王國延壽十四年至唐代宗大曆六年這一百三十多年間,吐魯番地區的浄土信仰,是廣義還是狹義,仍然不甚清楚。而本文所舉五件世俗有關浄土的《功德疏》,均屬唐代前期,正好作爲探討該時期吐魯番地區浄土信仰的絶好材料。
這五件《功德疏》所列功德,包括講(説)經、誦經、讀經、轉經、寫經、燒香、受戒、齋日、設供、布施、造幡、燃燈、畫佛、造像、行道、禮佛名、造廳堂、塑畫變相等。這些功德大致均與浄土宗的修行内容有關。我們可以先根據傳世文獻和其他出土材料,對這些功德進行印證,説明該時期吐魯番地區功德做作和浄土信仰的情況。
(一)講(説)經。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唐貞觀二年(年),三藏法師玄奘西行求法,途經高昌,曾被高昌王麴文泰挽留,講《仁王般若經》達一月之久。當時,“王别張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别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昇法座,王又低跪爲蹬,令法師攝上,日日如此”。按:《仁王般若經》全名爲《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此經因宣傳如何鎮護國家,祈禳災變,頗爲統治者所重視。歷代統治者多有“仁王法會”之設。高昌王麴文泰特請玄奘講説此經意義相同。雖非浄土經典,但可見該地區講經之盛。
(二)讀經。吐魯番哈拉和卓某墓出有一件《唐寫本大般涅槃經題記》,該題記部分爲“讀《大般涅槃經》日曆”,詳記某人從某年十月至翌年三月讀《大般涅檠經》多達九遍的流水帳[35]。
(三)轉經。吐魯番阿斯塔那號墓出有一件《武周證聖元年(年)五月西州高昌縣崇福寺轉經歷》,殘存二片,共57行,詳記當年五月西州高昌縣崇福寺新舊僧徒逐日轉讀《法華經》和《大智度論》的情況(文書八,~頁;圖文肆,~頁)。按:《大智度論》是解釋《大品般若經》(全名爲《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專門著作。《大品般若經》因有“浄土”、“往生”等品,頗受浄土宗重視。又,阿斯塔那號墓出有一件《唐某寺都維那惠童牒爲寺僧轉經歷》,殘存8行,記唐某年西州某寺僧徒“終而復始”轉讀某經(名稱不詳)的情況(文書九,~頁;圖文肆,頁)。
(四)寫經。從麴氏王國延壽十四年(年)至唐代宗大曆六年(年)這一百三十多年間,吐魯番出土的佛教寫經數量繁多,其中,紀年明確的重要寫經有:高昌延壽十六年(年)寫《大方等如來藏經》、唐顯慶元年(年)寫《妙法蓮華經》、武周久視元年(年)寫《彌勒上生經》、唐乾元元年(年)寫《金剛般若經》、唐廣德二年(年)寫《四分律行事鈔》。紀年不明確的重要寫經有:比丘惠德寫《妙法蓮華經》、麴敬□寫《般若心經》、白衣弟子高某寫《妙法蓮華經》、西州司馬麴某寫《大智度論》。有的爲浄土宗經典,有的爲其他佛教宗派經典[36]。
(五)受戒。吐魯番出土一件《唐寫本般若心經題記》,首稱“菩薩戒弟子麴敬□”[37]。此類例證甚多,不贅舉。
(六)齋日。吐魯番阿斯塔那74號墓出有一件《唐衆阿婆作齋名轉帖》,殘存34行,記唐某年西州某地二十六位阿婆各出大麥若干爲“月别齋日共衆人齋”事(文書六,~頁;圖文叄,81~82頁)。又,大谷文書號《唐代浄土教徒祈願文》記有唐某年西州某地大嫂、老妻、兒女等取油供奉設齋事,又屢見“每歲之中有三長齋”“爲大齋之日”“正法受持齋戒”等語,恐怕也是一件與齋日有關的文書。
(七)禮佛名。東京靜嘉堂文庫所藏吐魯番出土唐寫佛經斷片中,頗多“佛名經”斷片。説明禮佛名在當時吐魯番地區十分流行。
(八)塑畫變相。如前面提到的《絹本浄土變相圖》[38]。另外,德國探險家在吐魯番勝金口石窟的天井及壁畫中也發現唐代的“浄土變相圖”[39]。説明當時吐魯番地區塑畫浄土變相非常普遍。
以上僅從《功德疏》所列衆多功德中選擇八項進行印證。雖然并不全面,但可以認爲,該時期吐魯番地區的功德做作非常普遍。這應是該時期吐魯番地區浄土信仰深入人心的真實反映。
另外,這五件《功德疏》所列功德,主要爲講(説)經、誦經、讀經、轉經、寫經,記録佛經甚多。我們可以再根據疏中所舉佛經,結合其他功德,探討該時期吐魯番地區浄土信仰的形態。
第一件出現最多的爲法華經,凡三見。該經如前所説,由於涉及彌勒和觀音,爲彌勒門派和觀音門派所重視。另外,該經極受彌陀信仰鼓吹者竺法曠推崇,又爲彌陀門派所重視。涅槃經一見,灌頂經二見。此二經與法華經相似,也爲浄土宗各門派所共同信奉。金剛般若廣略一見。前文已有解説,此處不贅。又,消伏經一見,觀音經二見。此二經卻爲觀音門派重要經典。這似乎顯示,疏主董真英的浄土信仰,廣義的因素較少,狹義的因素較多。疏主董真英有意偏重觀音門派,大概與自己爲女性,而民間相傳觀音亦爲女身有關[40]。因爲這五件《功德疏》,疏主三男二女,三男之疏均無觀音經,二女之疏(即本疏和第四件阿婆疏)均有觀音經,應該不是巧合,由此證明,當時的吐魯番地區,已流行狹義的觀音信仰了[41]。
第二件出現最多的爲涅槃經,凡六見。此下,法華經三見,金光明經、大般若經、金剛般若經各二見,對法論一見。但這些經,如前所説,反映的均屬廣義的浄土信仰。又,新婦曾發願,云:“須覓生天浄佛國土,不得求人間果報。”其中“浄佛國土”出《妙法蓮華經》第四《信解品》,與《維摩詰經》第一《佛國品》所云:“若菩薩願得浄土,當浄其心,隨其心浄則佛土浄。”意義大致相同,反映的也屬廣義的浄土信仰。但又見隨願往生經。疏主阿公死後,曾根據隨願往生經做作懸幡、燃燈、轉讀等等功德。同時,請僧懺悔,又曾根據隨願往生經,祝阿公“合得十方浄[土]”。似乎阿公本人對十方諸佛門派頗有興趣。另外,根據疏主阿公生前功德,似乎阿公本人對彌勒門派更情有獨鍾。如阿公曾“泥塑彌勒上生變”,并“布施百丈彌勒”。又,據阿公曾“施彌勒佛玄覺寺”,知此玄覺寺爲彌勒門派寺院。阿公又曾專“造一廳並堂宇,供養玄覺寺常住三寶”。可見阿公本人對彌勒門派信奉之深。按吐魯番地區有專門的彌勒門派寺院,并不始於西州,可以追溯到高昌時期。吐魯番出土麴氏王國時期《諸寺田畝帳》中即有名爲“天宫寺”的彌勒門派寺院(文書五,頁;圖文貳,頁)。綜上説明,當時的吐魯番地區,又一直流行狹義的十方諸佛信仰和彌勒信仰。但對疏主阿公本人而言,既信奉十方浄土,又信奉彌勒浄土,這種浄土信仰,仍然是廣義的因素居多。
第三件僅出現一經,即盂蘭盆經,反映的似屬廣義的浄土信仰。但疏主左憧憙生前曾“造壹佛、貳菩薩”,若非“彌勒三尊”,即是“彌陀三尊”,反映的又屬狹義的浄土信仰。
第四件出現最多的爲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見。此下爲法華經、涅槃經、金光明經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各一見。這些經,如前所説,反映的均屬廣義的浄土信仰。又有隨願往生經,亦二見;觀世音經,亦一見。此二經反映的則屬狹義的浄土信仰,亦即十方諸佛信仰和觀音信仰(參閲以上關於第一件和第二件的探討)。但對疏主阿婆本人而言,既信奉十方浄土,又信奉觀音浄土,這種浄土信仰,也仍然是廣義的因素居多。
第五件出現三經,爲法華經、金剛般若經和大方廣佛名經。前二經反映的均屬廣義的浄土信仰。後一經性質應該相同。我們知道,浄土宗修行内容之一爲“稱名”,亦即念誦佛名。佛名經就是專爲這種修行而設。這種經廣記佛名,反映的應該亦屬廣義的浄土信仰。
通過對這五件《功德疏》所舉佛經的初步探討,可知該時期吐魯番地區的浄土信仰是狹義和廣義兼容,狹義的因素較少,廣義的因素較多。狹義的浄土信仰主要爲觀音信仰、彌勒信仰和十方諸佛信仰。觀音信仰似乎主要爲婦女信奉,且均有觀音經爲證。彌勒信仰雖未見所謂“彌勒三部”,但有根據彌勒上生經泥塑的“彌勒上生變”。吐魯番地區的鄯善縣曾出土武周久視元年(年)西州交河縣龍泉鄉氾德達請人抄寫供養的彌勒上生經殘卷[42]。證明該時期吐魯番地區的彌勒信仰、尤其是彌勒上生信仰確實十分流行。十方諸佛信仰由於包括所有美好,似乎更受庶民歡迎。但如果既信奉觀音浄土,又信奉十方浄土;或者既信奉彌勒浄土,又信奉十方浄土,這樣就又變成了廣義的浄土信仰。我們認爲,該時期吐魯番地區的浄土信仰,雖然狹義和廣義兼容,但狹義的因素較少,廣義的因素較多,含義正在於此。而同一時期,卻不見彌陀信仰流行的迹象。我們知道,這一時期,中原的彌陀信仰,由於善導等人的大力鼓吹,不僅十分流行,而且逐漸佔據浄土宗的統治地位。吐魯番地區雖然遠在西疆,接受中原文化,往往較一般地區爲晚,但同一時期,該地區完全不見彌陀信仰流行的迹象,也是很難理解的。況且,到唐代中期,該地區彌陀信仰確實非常流行,此前也應有一個漸變過程。因此,恐怕在此之前,彌陀信仰與前舉觀音信仰、彌勒信仰和十方諸佛信仰一樣,也曾在吐魯番地區流行,不過因爲出土材料有限,不爲我們所知罷了。只是需要指出,當時的吐魯番地區,彌陀信仰即使流行,也與前舉觀音信仰、彌勒信仰和十方諸佛信仰一樣,并不意味已成爲狹義的浄土信仰,極有可能也變成了廣義的浄土信仰。總之,我們認爲,在唐代前期或者説在麴氏王國延壽十四年至唐代宗大曆六年這—百三十多年間,吐魯番地區的浄土信仰,狹義的因素較少,廣義的因素較多。這與隋唐時期整個中國的浄土信仰又由廣義變爲狹義的傳統觀點不合,亦與公元7世紀以後彌陀浄土佔據浄土宗統治地位的傳統觀點違悖。
綜上對唐西州前期五件《功德疏》的詮釋和探討,可知在唐代前期,西州庶民的浄土信仰,與中原并不完全相同。當時中原庶民的浄土信仰,已由廣義變爲狹義,彌陀浄土佔據了浄土宗的統治地位。而西州亦即吐魯番地區庶民的浄土信仰,卻仍停留在廣義階段,觀音信仰、彌勒信仰和十方諸佛信仰並存,彌陀信仰反而不顯。究其原因,恐與西州亦即吐魯番地區遠在西疆,接受中原文化較晚,又習慣維護自己固有文化有關。譬如:第二件《功德疏》所列功德有“衆人出八十疋帛練,畫維摩、文殊等菩薩變一鋪”。這顯然是根據《維摩詰所説經》第五《文殊師利問疾品》所畫的變相。而據對敦煌壁畫“維摩變”的研究,以該品爲變相題材,主要在初唐以前;初唐以後,人們的興趣轉移到該經《佛國》《弟子》等品,以維摩、文殊爲中心人物的變相已十分少見了[43]。這也説明,西州亦即吐魯番地區,其文化的發展,由於上述原因,不僅與中原,就是與近鄰敦煌也并不同步。這種文化特徵,應該引起我們注意。
後記:
本文發表於年,此次制作
转载请注明:http://www.tulufanzx.com/tlfszx/6305.html